6月17日,我乘航班飞赴宁夏银川,应邀参加于次日举办的“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8周年暨首届水洞沟文化旅游节”活动。随身带了一本金一南先生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撰写的书——《苦难辉煌》,意在伴我度过1个半小时的空中旅程。当飞机穿越了毛乌素沙漠后即将降落银川河东机场,舷窗外变换的景色把我从书页上吸引开来——先是长蛇一般的土黄色长城把耀眼且绵延的黄色沙海和暗淡了色调并被沟壑切割得条条块块的黄土高坡截然地分成一副苍凉画卷的两半,随后那皱纹纵横的荒原又一下子泾渭分明般地与一碧万顷的绿色田野嵌连。而一条黄色的大河,凝重地从绿野中蜿蜒流过,把其色泽源出之荒原与其乳汁浸润之沃野融为一体。
这“天下黄河利宁夏”而成的独有景观令我心潮澎湃。尤其是在跨越长城的时候,我的心随着眼睛贪婪地搜寻。我知道在长城脚下的某个沟壑周围,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水洞沟,那个一万至三万年前的先人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18日上午,“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8周年暨首届水洞沟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的各项活动在东距银川30余公里的水洞沟进行。当大型画册《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首发式举行的时候,我蓦然感受到了其与众之不同。
不同,就在于她被冠以科普之名,要知道,在我们中国,以旧石器考古为主题的科普画册真可谓凤毛麟角!
强烈的好奇让我在开幕式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就“抢”来一本画册,利用别人去景区游览之际和午餐前后的休息时间,躲在新建成开放的“水洞沟遗址博物馆”后门口的阴凉下,一口气“读”完了全书159个页面上的300多幅图片,以及这些图片的说明文字。
令我叹为观止的,首先是那些水洞沟地区自然景观的照片。在这里,陡立的黄土崖、鬼域般的雅丹地貌、黄色波涛似的沙漠,无不展现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力量。长城、烽火台、古城堡等遗存,则把自然与人类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一起。而各个旧石器考古遗址所处的地层剖面,通过摄影者颇具匠心的镜头表达,使其在反映科学内涵的同时张显着西北汉子般的野性之美。鲜明对比之下,那些荒漠里顽强生息着的红柳、蓟草、锦鸡儿、沙葱、羊群、沙蜥甚至蝗虫,都把生命的倔强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多水的沟谷里葱茏的芦苇、蒲草以及悠然其间的白鹭、长脚鹬、蜻蜓、豆娘甚至是蜘蛛和花蛇,更是以生物世界的欣欣向荣给这个世界展现着希望。
这些照片的摄影人,都是常年在水洞沟地区默默地考察、发掘的考古工作者,而且绝大多数都只有二三十岁。我知道他们每天在骄阳下或是风雨中的野外工作是多么地辛苦与单调,可是这一幅幅画面,让我看到了他们执着于科学事业的同时内心深处涌动着的青春的冲动、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美的追求。这,怎能不令我肃然起敬。
美伦美奂的景物之外,画册里更多的是记录水洞沟遗址从发现伊始至今近90年来的科学考察和野外发掘的历史过程,以及相关的科研成果的积累。从中,我了解了桑志华和德日进两位法国科学家最初发现这个遗址的重要意义,了解了后继的一批批科学工作者对水洞沟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一次次进展,了解了水洞沟旧石器文化作为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节点的特有学术价值。在当今这个读图时代,能够让我这样一个旧石器考古的门外汉主要通过欣赏画面就得到了如此系统而全面的收获,而且大大地激发起我对旧石器考古的兴趣,这本画册完全实现了其“非传统、非纯学术”地引领“公众考古”的目的。
掩卷沉思,我脑海里蓦然回放出飞机上读的那本《苦难辉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一段名言竟然响彻在耳:“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此刻,坐在“水洞沟遗址博物馆”之侧,放眼前方逶迤的水洞沟和各个旧石器考古遗址,一个强烈的念头闪现出来:毛泽东形容长征的三个形容,如果针对中国旧石器考古事业来表达水洞沟,那是多么地贴切呀!
水洞沟是宣言书。当之无愧!正是由于桑志华和德日进1923年在水洞沟发现了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连同他们在距此不远的萨拉乌苏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一起,确认了中国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从而宣告此前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在5000年前那样古老的时代不可能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指仰韶文化),更不要说可以追根溯源到旧石器时代”这个主观臆断的终结。同时,水洞沟的发现也宣告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诞生。
水洞沟是宣传队。恰如其分!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一次次的发掘、一步步的科学研究、一个个科研成果,逐渐揭示了“3万~1万年间古人类技术特点、生存模式、智能发展、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以及古人类演化的气候环境背景”。与此同时,这些科研成果转化而成的知识要素,已经渗透进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的头脑里。尤其是这本画册中大量体现的2002年以来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取得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不仅以各种科普手段丰富了广大公众的知识库,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史前考古的深层次思考、探索和实践。其中,水洞沟旅游景区的开发已经为史前考古学科研成果向文化产业的转化开创了一条路子。相应地,充分认识旧石器考古遗址的重要性,唤起全社会的觉悟来保护好这些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尽资源,这样一种理念也已经通过水洞沟、通过这本画册广而告之了。
水洞沟是播种机。毫不夸张!桑志华、德日进之后一个又一个旧石器遗址在中国的发现,一代又一代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的成长,有谁敢说与水洞沟的开创性工作没有关联呢?进入21世纪以来,水洞沟的播种机作用再一次发扬光大。2003年及随后的4个年份,每年的夏秋时节都有一支朝气蓬勃的考古队伍来到水洞沟开展他们的“快乐考古”。队伍里除了如本画册第一、二位主编那样的少数几位中年科学家和长者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各个研究所和大学考古院系的青年科技人员和学生,前后参加发掘工作的年轻人竟然超过了100人次。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全新的旧石器考古学实践。从周密的前期调研和设计,到制定明确的发掘目标和完备的发掘计划;从实行多学科交叉,到利用现代田野工作先进仪器和设备,力图进行全方位、系统地采集遗址中的一切可能的材料和信息,以复原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和生存环境。在水洞沟这所田野学校,这些年轻人充实了知识、积累了经验、丰满了羽翼。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各自科研领域和科研岗位上的栋梁。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现在就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这本画册已经记录下了他们的艰辛与汗水、他们的惬意与欢乐。对他们自己,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这些画册的读者,他们的每一个笑脸或是专注于工作的神情都赢得了一份羡慕、一份钦佩、一份向往。这些记录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小照让我又想起了另一本与中国工农红军有关的书——《西行谩记》,书中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一幅幅不论是领袖、指挥员还是普通一兵印刻在历史的一瞬间的不朽的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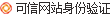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