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刘正奎

汶川地震后,大学生帮助孩子们进行逃生技能和心理应对的训练。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灾害心理援助与创伤研究”青年创新团队组长
●澳门赌场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
据媒体报道,来自昆明的杨先生在经历过“3·1”昆明暴恐案之后,5月6日在广州噩梦重演,当时他刚刚乘坐K366次列车到达广州,出站就遇到“一个青年挥舞着砍刀向他跑来”。杨先生丢下行李拔腿就跑,之后的两小时,“瘫坐在广场,惊魂久久未定”。
“恐怖袭击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是无边界的,它对亲历者的心理伤害远大于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至少有因可循。”澳门赌场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灾害心理援助与创伤研究”青年创新团队组长刘正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恐怖袭击案件对人们安全感的伤害非常大,“一定要对亲历者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
“当时杨先生瘫倒在地两个小时,可见这对他而言是非常强烈的心理打击,处于崩溃的边缘。”刘正奎说,“如果在昆明暴恐案之后,杨先生经历了积极的心理干预,过了这个坎儿,那么他面对广州砍人事件的时候会从容很多。”
刘正奎告诉记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之时,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居民并没有陷入恐慌:“汶川那么大的灾难都挺过来了,这又算得了什么?”
“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创伤,挺过来之后的这些人再次经历类似的事件,能够表现出更强的抵御能力,所以应该对灾害亲历者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帮助他们迈过心里的坎儿。”刘正奎说,“为什么打仗的时候老兵的战斗力更强?就是这个道理。”
应急心理干预在行动
刘正奎介绍说,定位于“应急心理干预小组”的“灾害心理援助与创伤研究”青年创新团队以澳门赌场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为依托,由专家学者、专业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专业社会义工等组成专家组,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灾后心理救援工作。
“心理援助与常规救灾不同,常规救灾工作一般两个月就结束了,而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这期间需要调动的人员非常多,所以我们的办法是在灾区建立相适应的工作站。”刘正奎说,当地医院、教育单位以及社区是他们开展工作的“据点”。
“我们会有针对性地联合当地(受灾地)医院建立一个心理科,通常是我们派专家去医院,一边提供心理援助,一边培训相关人员,通过2~3年的努力,逐渐形成常设心理科室。”刘正奎介绍道,在学校等重要环节,团队的做法主要是联合当地教育局建立心理援助工作站,“这个工作站主要为当地学校师生服务,如灾后师生的心理康复等,同时培训骨干教师心理干预方面的理念和方法,希望在3年之内形成一个当地的心理救助力量,慢慢演变成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变成当地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在社区的心理救援工作相对而言较为“基层”。“一般情况下我们与社区基层党委合作,最初是去灾区临时搭建的帐篷、板房里做一些居民的走访,发现重点人群并进行积极的干预;然后组织社区活动,加强社区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我们招募当地志愿者介入,经过3~5年的培训和历练,成立当地的NGO组织,把后期的工作交棒给这些组织。”
“工作站的好处在于,老百姓知道去哪儿寻求心理救助。”刘正奎说,“有些人不习惯去医院,那么扎根于学校、社区的工作站就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很多问题。就算有些问题无法解决,工作站也能告诉他们应该去哪儿、找谁解决。”
刘正奎说,团队的目标是 “等专家团队撤出灾区的时候,心理救援的队伍也建立起来”。
目前,团队已经在北川、绵竹、什邡、德阳、舟曲、玉树等地培养出了一批活跃的队伍,这批队伍不仅能够满足当地的心理救助需求,还能在临近地区发生灾害时,第一时间提供相应的心理救援工作。“雅安地震的时候,北川、绵竹、什邡的心理救助队伍就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目前芦山的很多心理干预工作还是他们在承担。”刘正奎告诉记者,“队伍越来越大,我们的工作就越来越有信心。”
心理救援亟待常态化
由于心理援助的特性,其救助范围比较广泛,既有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救治,又有对一般心理问题的疏导,加之具有社区功能属性,所以心理援助至少横跨了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工作。
“心理障碍大部分是由于事件冲击带来的系统性问题,涉及范围比较广。”刘正奎认为,“保障服务相当于教育、卫生部门各自增补当地的心理干预服务项目,加上立足于服务社区的NGO组织,有这样的队伍保障,才能够做到自我救助。”
此外,心理救援工作站除提供一般性服务之外,更要有专业的心理治疗,要做到两个层面都要兼顾。“只有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并最终纳入当地的组织体系中,才能确保心理工作的长效性。”
“心理工作常态化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当地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二是能够纳入当地组织体系。”刘正奎指出,这种分层的结构,既有民间力量参与,又有官方的协助,“把民间和官方体系打通,在未来发生类似恶性灾害的时候,才能发挥持续性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整个救助体系中,心理救援这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刘正奎告诉记者,尽管国家减灾委《关于加强自然灾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将社会心理援助作为自然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一部分,但在机制层面和政策层面仍缺乏具体的规范。
发展中国灾难心理学体系
“建立心理援助服务站、工作站,对于心理学研究也有反哺作用。”刘正奎说,“我们最近在作灾难心理学的研究,我认为这项工作对于中国的灾难心理学体系的发展是一种推动。”
他告诉记者,目前心理治疗的很多方法都是采自国外,不一定适用于我国。“除突发性事件导致的生理变化外,一定意义上,心理方面的问题属于文化产物。”
刘正奎说,面对突发的灾难事件,人在受到惊吓、打击等心理冲击后,都会体现出激素水平异常等的变化,而如果冲击过大,有可能造成神经系统的损伤,此时人们容易产生恐惧感、对事件的回避或者麻木,这种心理冲击带来的负性情绪是共性的。“但是康复的时候会受文化理念的影响。康复治疗既要利用通用的科学手段,比如放松、生物反馈、药物治疗等,也要考虑大部分人可以利用文化的认同感等力量,进行有效干预和自我康复。”
“有很多文化元素,包括音乐、仪式等,都是处理这种情绪的载体。西方的处理方式跟我们就不一样,通用科学之外,文化影响也有很多。比如西方的心理干预起源于基督教的牧师制度,而我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要发展中国的灾难心理学。”刘正奎告诉记者。
中国是一个多灾难的国家。近一百年来,全球伤亡人数最多的十大灾难中国占了四起,这其中包括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
此外,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灾害频繁程度加大以及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导致的灾害对国人的威胁越来越大,长效的灾后心理救援体系越发显得必要。
位于美国丹佛大学的国际灾难心理学中心,设有灾难心理学专业,每年那里的硕博士都会来我国交流;日本与我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也比较多,汶川地震、日本“3·11”大地震期间双方互有交流和帮助。“涉及到学科研究和培养人才,我们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发展这一学科,至少在东西方文化氛围的区别之中,作适用于中国的心理科学研究。”刘正奎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4-05-30 第15版 纵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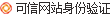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