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赵林的相见多少有些意外,坐在车上发现司机竟然是他。
车上的人大都是第一次进高原,大家谈兴甚浓,但当看到一个山峦连着一个山峦,似乎永无止尽时,车内顿时沉静下来。后来,不知谁说,看到灯光就到了,于是大家又开始盼着能看到灯光。
没想到这一盼,竟盼了18个小时。
从西宁至格尔木,近800公里,除了中间偶尔的一段换人外,司机始终是赵林。
赵林是藏北高原冰冻圈特殊环境与灾害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以下简称格尔木站),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寒冻土方面的基础研究,他的“办公室”就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大学毕业至今的26年里,他以每年至少2个月,每次至少1.6万公里的频率走遍了青藏高原的三省区。
800公里挺进高原,对于平常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长途奔袭,对赵林来说却只是家常便饭。
苦乐交错中拥有一颗朴实无华的心
“3000米以上无大小,4000米以上无男女”。
这是记者听到的第一句形容野外生活的话。当时以为是句玩笑话,然而在跟随赵林前往海拔4636米的五道梁观测场的路上却深切感觉到了苦乐交织的感觉。
雄伟的昆仑山,甘冽的圣泉水,圣洁的玉珠峰……无疑让人心旷神怡,然而紧随而至的高原反应让人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呕吐、头晕、四肢乏力使几个同行的女同志止步在海拔4538米的西大滩观测场。
“在高原,有一首民谚:‘高原气候变无常,一日需备四季装;山上鲜花山下雪,中午烈日早上霜’。意思是说你永远不知道前方有什么,下一秒要发生什么。”进高原之前,寒旱所党政办副主任岳晓这样给大家打“预防针”。
但当记者真正身处五道梁野外工作点时,还是被眼前所见的一幕惊呆了,入目的是极为简陋的帐篷,除了住人外,还堆放着各种设备和杂物,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一阵狂风吹过,东西被吹得七零八落。
多年跟随赵林出野外的工程师乔永平告诉记者,冻土监测主要在冬季进行,那种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是最考验人的。
“哪怕你武装到了牙齿,你所面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改变。你照样得忍受5000米以上严重的高山缺氧,举步维艰倒也罢了,还要不时竭尽全力推挖泥泞中的陷车,还有每天下午必起的大风沙,被雪掩埋的帐篷里普遍的失眠……”乔永平的讲述让记者顿生感动和敬意。
即便如此,赵林还要进行一天至少四次的钻孔、放探头、取数据。也因此,他的脚患上了脉管炎,医生警告他再受冻可能就要截肢。
当记者提出看看他的伤脚时,他只是略微抬了一下就收了起来,并以此开起了玩笑:“西医说60%没治了,中医说60%可以调理,不管怎样,病情得以缓和,后来我自己也看起了《黄帝内经》,期望不再复发。”
还能出野外,成了他最开心的事。
多少人劝他,也有人质疑。
图钱?出野外的补助每天每人包含吃的也就200元钱,经常不够花。
图名?他发在全球冻土界最高级别杂志《多年冻土与冰缘过程》的论文2013年进入全球下载TOP10,成为国内在冻土领域前20名的科学家的信息全是别人告诉他的。
对此,他说:“登山界有句名言,‘为什么去登山?——因为山在那里!’对于我们研究冻土的,数据是最重要的,数据在哪里,我们的人就应该在哪里。”
用心做事中坚守科技人员的本分
赵林说,他始终忘不了父亲的教诲——当个本分人,更忘不了研究生导师邱国庆的告诫——少说话,多做事。“我始终坚持一个信条:做人,就要把这个人立起来,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
用心做事,愿意付出,认真负责成了记者采访的诸多人中对赵林评价最多的几句话。
格尔木站副研员焦克勤告诉记者,赵林对站里的建设非常用心,刚建站时经费少得连维持基本的科研都不够,更别说改善生活条件,后来通过努力陆续申请了不少课题,钱多了大家都想着能发些补贴,改善一下住宿条件,然而赵林却全买了设备。
“当时很多人骂他傻,老赵却说,干咱们这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才是最重要的,吃的差点,住的差点没什么。”在焦克勤看来,赵林的心里只装得下科研。
说到数据,助理研究员岳广阳同样感触很深:“赵老师对数据很看重。当你取得一组严谨、可信的数据时,赵老师会笑得很开心,当他发现你的数据有问题马上会板起脸。我们的论文他都会亲自看,感觉没有观点的,他会要求我们重写,尽管有时我的心里极不愿意。”
“不准乱发论文,要发高质量论文。”岳广阳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接受了这个理念。
赵林补充说:“每件事都要想一下合适不合适,发没有多少进展和亮点的文章,就是对科学的不尊重。”
在好朋友吴青柏看来,赵林有些“直”得过分。他记得有一次院里要申报一个项目提出把赵林的课题也列进去,赵林断然拒绝了。
“我的项目已经结题了,这个项目才开始,怎么能算到里面去。科学家不说真话,谁还说真话。”提起此事,赵林依然认为自己没错。
赵林任站长不到10年,格尔木站由最初的2人,发展到现在的20人,而且汇集了多个学科——搞生态的、植被的、数据的。
吴青柏认为,这个成绩与赵林所坚守的科技人员的“本分”不无关系。
探索开拓中占领冻土科研的前沿
人们常用雄伟、辽阔、壮丽之类字眼描绘青藏高原,紧跟着还有一词:“神秘”。对于外人来讲,多年形成的、活动层厚度小于2米的寒冻土则显得更为神秘。
赵林给记者看了一张他新编制的多年冻土图,对比1996年李树德等编制的青藏高原西部多年冻土分布图,记者很快发现了其中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赵林说,近20多年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以前的资料有不确定性和不准确的找出来,搞清楚。
“因为之前我们所用的有关青藏高原寒冻土的数据尽管参考了中国的数据,但没有一个是由中国发布的,且这些都是表面化统计,究竟青藏高原寒冻土过去有多少,现在有多少,未来有多少,以及冻土与气候、与生态的关系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我相信这项科研对未来生产生活一定有用。”
基于此,赵林承担了青藏高原的多年冻土本底调查项目,特别是对一些典型区域,比如可能修路的,有工程的地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都给出了剖面图或分布图。
赵林如此表达自己对寒冻土研究的期望,“我希望以后用到青藏高原地表参数方面的数据能由我们格尔木站代表中国发表,并能够得到国际认可;我希望在所有模式中用到地表过程描述方面的参数或者要分析寒冻土变化机理,能用到我们给出的公式;我也希望我所研究的多年冻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状况,以及青藏高原寒冻土会向什么地方变化能有所成果……”
尽管实现这些复杂而艰难,但对赵林而言,是挑战也是诱惑。“不管怎样,向寒冻土未知领域的探索我会始终坚持下去,我相信离目标不远了。”
也许,这份坚守就是赵林想要书写的美丽人生。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4-07-23 0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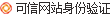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