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星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给60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今天其他任何一个在世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
“古生物”三个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过于遥远,更是毫无趣味可言;但说到恐龙,却颇受大家欢迎。也因此,和恐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徐星并不孤独,他不仅有自己钟爱的科研陪伴,还有诸多的恐龙爱好者支持,他们会在网上编辑“徐星发现的十种见证恐龙向鸟类过渡的新物种”之类的帖子。
徐星现在是澳门赌场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生代恐龙化石及相关地层学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兽脚类恐龙的形态学、分类学和系统发育、鸟类起源等。他在1999年提出并纠正了美国《国家地理》“古盗鸟”错误报道,并在2001年入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徐星被称为古生物界的“中国星”,《自然》杂志2012年曾为他写下过这样的评语:“徐星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给60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今天其他任何一个在世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并且他今年只有43岁。”
虽然今天徐星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颇有建树,但与许多迷惘于要不要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大学生一样,学生时代的他也曾犹豫要不要从事这份“前途渺茫”的工作。
“我们那一代,婚姻都是先结婚后恋爱。”平时就以会讲故事、将复杂的问题化繁为简知名的徐星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科学起初于我也有点像婚姻,首先是我的责任和日常生活。”
先结婚后恋爱未尝不是一个好答案,起码截至目前徐星与恐龙的“恋情”依然甜蜜。
纠结
出生在新疆新源县的徐星祖籍江苏,父母参加江苏大中专支边团支援边疆后在新疆定居。在信息闭塞的小城里,读书为他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尽管生活并不富裕,父母还是会用各种各样的图书堆满儿女们的日常生活。
上小学时,正逢陈景润因“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名声大噪,伴随这股热潮,徐星和全国诸多青少年一样,立志要当个数学家;等到上中学,他又迷上了物理,立志要做个物理学家。与做个物理学家同样重要的是,徐星决心一定要去未名湖畔的北大读书。
天意弄人。偏偏徐星高考那年,北大物理系在新疆没有招生名额,仅有的几个名额也都在冷门专业。徐星已经不记得自己填报的具体是什么专业了,但“肯定不是地质学”——为了进北大,他也在“服从分配”前面划了勾。
录取通知书一到,发现录取自己的是“古生物专业”,当时全家人包括学校老师都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是干什么的,直到入学之后才了解是地质学下面的一个专业。对此毫无兴趣的徐星希望能够转系,最后发现“此路不通”,只得寄希望于考研。
大学时代,徐星读了更多的“大部头”——萨特、维特根斯坦、马克思、萨缪尔森等著作,统统来者不拒。“毕业前一年的八月我开始到人大旁听”,他盘算着将来读一个国际金融之类的经济学专业。
也正在这个时候,学校开始推荐研究生。“我在班上成绩不是靠前的。前面的都留本校了、换专业了,我就来澳门赌场研究生院了。”
其实,在接受免试推荐的过程中,徐星颇为“纠结”,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命中注定的“缘分”。
在澳门赌场,徐星跟着古生物专家赵喜进先生读硕士生。当时国内做恐龙研究的人非常少,在开头的两年里,他依然“不务正业”,迷恋计算机。直到研究生阶段的第三年,迫于毕业论文的压力,徐星才真正进入角色,在专业领域里有所深入。
好的标本让他慢慢感受到了恐龙的魅力,渐渐地,徐星才真正开始对自己的专业产生兴趣。他和导师赵喜进共同完成了对当时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角龙类“朝阳龙”和最早的镰刀龙类“峨山龙”的研究,论文最后分别发表在美国的《古脊椎动物学报》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这是徐星第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而这样重量级的认可也给了他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和鼓励。
磨炼
2001年,徐星入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了国家基金委80万元的资金支持。
“‘杰青’是第一笔在国内申请到的大额资金,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是独立承担科研项目的开始。”尽管在最终报告时因为电脑故障闹了一点“乌龙”,徐星还是凭借亮眼的工作表现入选最终名单。
基金的一部分用于辽宁热河生物群的研究,其余的部分几乎全部用在了新疆、内蒙古等地的项目上。
“我们作野外研究,经常要去很偏僻的地方,有机会看到落后地区的情况、农民的屋子有多么原始,会被看到的东西刺激到。”如果让他花掉一两万的版面费,徐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他说:“作研究的人本身要有良心,用的是老百姓的钱,花钱的时候要想到这个事情。”
化石发掘是古生物研究的第一环,中国因为丰富的化石资源而备受世界各国古生物学家的欢迎。也正因如此,每年的野外考察,徐星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参加申请。
一群人在戈壁沙漠工作不是件风花雪月的事情,头顶骄阳的野外工作更多需要耐性和毅力。徐星不洗脸的最长记录是一个月,还有袜子“站”起来的经历——汗水里的盐分越累越多,最后硬到了这个程度。
惊心动魄的经历更是偶有发生。迫于经费所限,大部分时候他们不能租借装备精良的车辆;而野外恶劣的路况,经常让考察队的车子抛锚。“从大山坡上冲下去,因为路太颠簸,刹车管都被颠断了。”最为夸张的一次是方向盘都断掉,“幸亏当时车开到了一个叫黄泥滩的非常平坦的地方,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一种危险来自地表上活着的野生动物。“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作为食物补给的羊被狼吃掉了。”毒虫之类的大家都是早已见怪不怪。
相比残酷的自然环境,更加让人倍感煎熬的是一无所获。但徐星好像天生带着好运,常常都会“有所得”,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在内蒙古二连这个上世纪50年代被前苏联用推土机找过的化石发掘地,徐星和同事50年后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似鸟恐龙巨盗龙;内蒙古西部单指恐龙的发现地也是一样,瑞典、加拿大、比利时等多个国家都在那里发掘过,唯独他的研究小组找到了世界上第一具单指恐龙化石。
好运总会眷顾执着的人。取得了好的标本,接下来就是马不停蹄地开始研究。那时徐星常常会兴奋到睡不着觉。这个过程讲究稳、准、快,有大量的数据要测算、大堆的表格要填,但没有什么比有所发现更能鼓励自己的科研。
有人曾经说可惜诺贝尔奖没有地质学奖项,不然徐星早就获奖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未来会不会有,徐星与恐龙的这场跨越时空的“爱恋”,不会终结。
跨界
如今的学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图书馆找到国际最新的专业期刊,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库查看到最新的论文成果。这些对于大学时代的徐星来说,都是十分奢侈且遥远的梦想。
十分有限的国内资源,让他想到了是不是可以运用互联网寻求帮助。他自己掏钱装了一个可以拨号上网的“猫”,将自己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写邮件请教专业领域内的知名专家。
这些邮件中的一些石沉大海,但也有些专家很快回复,并且积极地和他进行讨论交流。“这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现在徐星收到不知名网友的来信,总会尽量给予回复。
现在大家都喜欢讨论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徐星的“触网”经历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答案——互联网赋予每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
而从常见的“跨界”这个答案来看,徐星也是有话要说。去加州伯克利访问的时候,他注意到同行周围的合作伙伴来自各个领域——“有做生态学的、生物力学的,有做系统发育分析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你很容易找到新的研究问题或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相较之下国内在这方面十分薄弱。
今年五月的香山会议上,他和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开始讨论建立演化生物学会的可能性,让不同领域的学者有一个共同平台来讨论演化现象。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一起享受与恐龙的“甜蜜爱恋”。
记者手记
做完比完美更重要
采访徐星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不知是天性如此还是工作使然,这位古生物学家的言语和行动总会莫名让人觉得安稳沉静,善谈同时又很内敛。
办公室的空间被充分利用,靠墙摆放着书柜、沙发、桌子,“新鲜”的化石摆在茶几上,和一堆期刊放在一起。沙发后面的暖气片上除了各种书和资料之外,还有一副球拍和几只羽毛球。
墙壁很显眼的位置上有两幅儿童画,主题毫无疑问都是恐龙——一幅彩色,一幅只是简单的黑色线条。相比装帧精美的彩色图画,笔者的目光更多地被旁边仿佛是随便扯下来的白纸简笔画吸引,画的旁边歪歪扭扭地字是“画家”落款——蔡淙旭。徐星说这是他小学同学的儿子,因为看了他的某个节目开始痴迷恐龙。曾经每个月都要跟他汇报自己的情况。
徐星现在也带学生,古生物专业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是一个热门专业。他并不强求学生要发表多么厉害的论文,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亲身感知到有所发现的成就感。
如果有谁说想成为爱因斯坦一样伟大的科学家所以要来做科研,相较因为这样的宏图壮志而感到开心,徐星的反应更可能是忧心忡忡。“不要期望太高,要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
但如果太没追求,显然会成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农民需要种地,工人生产产品,基础研究就是要出论文。很多学生对自己‘产品’的预期超出实际情况,仔细、认真这都很重要,但不要想一篇文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做完比完美更重要。”
而说到准时完成任务,不得不提到一个让国内古生物学家略感尴尬的问题——我们发掘且进行研究的化石,往往会在国外的再研究中做出更重要的成果。
“过去世界不是很开放,给你时间细化;现在古生物的节奏很快,要求尽快地研究、出成果。初步研究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又来了一个新的东西。”徐星解释道,中国作为化石大国,自觉不自觉地会拣着“价廉物美”的先用。
从这点来看,中国人发现的化石被别人再研究出了成果——这是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在恐龙研究的“世界生产线”找准自己的位置,处于“先头兵”还是“后来者”的位置并不重要。
毕竟,做完比完美更重要。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4-08-01 第9版 人物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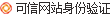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