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北京,微雨。早上8点30分,物理学家赵忠贤院士擎着把大伞,像往常那样,背着黑色的单肩包走进澳门赌场物理研究所M科研楼。在他的日程表上,今天多了一个让他有些为难的工作——接受记者采访。
“千万不要说我还在科研一线工作,这不符合实际!”赵忠贤说,“超导研究经常要自己磨晶体,在几毫米的材料上接线,这些活年轻人才能做。我现在眼花了、手抖了,就算在显微镜下也做不好。所以不能说我在第一线工作,千万不能!”
的确,不经意间,这位带领团队突破超导研究禁区的东北汉子已过了古稀之年。
从1976年从事该项研究至今,近4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很枯燥?”赵忠贤说,“我并不这么觉得。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我们做科研,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每天总是感觉更接近真理,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两次领导科研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发表论文近160篇,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当大家把种种赞誉都加诸赵忠贤身上时,他却说,“首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几十年来,团队成员或有变化,但踏踏实实、坚持不懈的精神并没有改变。“第二,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出现了人才断层,另外科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是空白的。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积累,我们只是比别人早开始了一些。就我所知,一些领域也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我相信未来几年,自然科学一等奖不会再交白卷。”
去年的一场病,让赵忠贤清瘦了许多,头发也白了。“现在不敢熬夜了,身体受不了。”赵忠贤说,“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超导研究已经走在国际前列,但这还不够。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没有提出过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新概念、新理论。”赵忠贤说,在超导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材料易,提出新概念、新理论难,要想让大家接受更难。”但只有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才能真正称得上从“跟踪”到“引领”的转变。“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实力,也有了丰富的积累,就看在哪个方向由哪个年轻人做出成果。”赵忠贤说,“这需要凝练学科方向、找准目标,也需要为年轻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让他们能安心做研究。”
“我鼓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赵忠贤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提出过和铁基超导材料的化学组成非常相似的材料,只不过用的是铜。“铁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能用作超导的材料,所以我压根没往那上想。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第一个提出铁基超导的或许就会是我们。”赵忠贤说,要创新,就要宽容失败,基础研究就是在不断的失败中找出一条成功的路。“但现在的评价体系对失败还是比较苛刻的,所以我尽可能为年轻人营造一个轻松的研究氛围,多承担责任,多呼吁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
“关于我个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只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赵忠贤爽朗地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只要大家说‘这个老头还不错’,我就挺高兴了!”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4-08-11 0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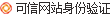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