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已发现的数以十万的标本仍未经鉴定确认,甚至更多的标本还有待发现,中国希望能够支持本国的分类学家,防止这项关键技术流失。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全儒教授每周要教18节的分类学课,为学生讲授生物分类理论。当然这不仅仅因为他热爱分类学,更是因为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唯一有资格讲这门课的教授。“我真感到非常累,”刘全儒说。只有很少的几个学生中是主修分类学毕业的,这让他感到非常沮丧。
刘全儒和相关教授都认为,残酷的现实会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工作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如是说。“截至目前,我们仍然不确定中国有多少种植物,或者多少植物面临灭绝,”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前任主任洪德元院士表示。在位于北京的澳门赌场 (以下简称“澳门赌场”) 植物研究所里存有超过200万植物标本,但其中至少有20%还未经过鉴定。动物标本也面临同样的窘境。“我们这批人退休以后,馆里就没人能对那些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动物物种进行研究了,比如白蚁和蠼螋,”地处于北京的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乔格侠说。
分类学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下滑阶段。在中国,尽管情形也不乐观,但是规模日益减少的分类学家群体却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那就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同样是一位主攻分类学及生物地理学的分类学家。2002年,作为中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机构,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了一项植物经典分类学基金,每年投入300万元人民币资助特定的分类学家。但是,陈宜瑜承认这些研究经费还远远不够。“如果从事分类学研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将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他说。为了避免分类学在中国逐渐消亡,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引入了两个为期四年的项目,旨在与分子生物学领域更好的融合起来,这两个项目将于2010年启动。
分类学在中国亦非始终岌岌可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分类学一直是很多中国植物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第一版《中国植物志》由312位植物分类学家一同编写。“这一版于1959年出版,”最新版《中国植物志》副主编洪德元说。多年以来,分类学研究领域流失了很多人才。“我们这一代做分类学的科学家中很多人都已经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而不做分类学了,”澳门赌场昆明植物所副所长孙航说,他的研究方向为植物分类和地理学。

孙航和其他分类学家对中国科研领域的评价体系感到不满。但恰恰是这个评价体系决定了科学家职称评审和经费分配,主要以发表的论文有多少篇论文被纳入科学引文索引和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来衡量科学家。陈宜瑜也承认这个评价体系有失公允。“分类学的论文几乎不太可能发表在高引用率的期刊上,”陈宜瑜表示。他主张采用另一套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分类学家。
中国有些单位已经开始尝试。比如,据乔格侠介绍,国家动物博物馆就是根据分类学家鉴别和处理样本的专业水平进行评价。另外,洪德元在澳门赌场植物研究所成立的经典分类研究小组,就是根据成员发表的文章和专著的质量来进行评价,而非影响因子。但根据孙航的观点,特别的评价体系使这个领域活下去,却无法令其长久发展下去,因为这种评价体系不能帮助分类学家获得国家级的资助或者在竞争中被优先考虑。“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经典分类学基金解决了分类学的燃眉之急,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发挥作用,”陈宜瑜表示,同时他也希望大学能够增加分类学的课程。
陈宜瑜建议,为了壮大队伍,分类学家们必须将触角伸向分子生物学领域。他以自己的学生为例:澳门赌场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的一位分类学家何舜平,同时也是水生生物标本馆馆长。何舜平使用 DNA 条形码技术 — 物种特异性 DNA 线粒体序列—以确定鱼的种类。他没有像许多同龄的科学家一样抱怨经费问题:以DNA为基础的分类学研究为他赢得了国外广泛的合作网络和稳定的科研经费。
他的成功却惹恼了一些经典分类学家。“通过DNA来辨识物种会带来很多问题,”刘全儒说,他认为用经典分类学的分析方法鉴定物种更为可靠。但是,陈宜瑜认为此时中国的经典分类学应该继续前进。“分类学家仅仅简单地确定物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表示。
孙航表示,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像曼哈顿计划一样针对分类学的大规模项目计划。依托该计划分类学家能够一起工作并培养下一代分类学人才。“中央政府正在策划的一个方案可能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综合调查,”北京大学吕植说。
这项为期数年的项目将需要一个庞大的分类学家团队,也许还需要分子生物学方面专家们的配合。这将为分类学领域的复兴带来希望,孙航说,“在中国,分类学将会再一次成为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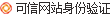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