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科学时报》发表何祚庥院士《中国会不会走向“半个”工业化?》文章后,不少朋友和领导想听听我对何院士担忧的看法,可见何院士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并不得不予以深入分析的重大问题。我拜读他的文章后的初步判断是:何院士的基本结论值得重视,计算方法则尚可完善,但碍于当时自己没有做过计算,故只能模糊作答。
3月9日,《科学时报》又刊登了陈俊武院士《就〈中国会不会走向“半个”工业化?〉与何祚庥院士商榷》的文章。陈院士是基本同意何院士观点的,即在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下,我国必须较快地降低单位GDP能耗,但完成此目标的难度颇大。同时,陈院士同何院士在计算过去几年减排强度上,所得结果有较大不同,尤其是陈院士的计算表明:我国2005~2009年的累积节能幅度只有7.4%,显然难以完成“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
与此同时,何院士建议《科学时报》拿出一定的篇幅,来深入讨论与此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为呼应何院士的建议,我们从CO2排放这个角度出发,对今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等作了分析与计算。首先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计算起点是国家确定的CO2减排目标这一“硬约束”。
2020年我国可以排放多少CO2?
我国政府作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承诺。根据我们的理解,对这个承诺首先需要明确两点:一是此排放特指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产的排放,不包括土地利用的排放,亦不包括生态建设的(固碳)负排放;二是GDP计量必须是2005年的不变价格,不能是名义GDP(即要排除通胀因素),并只能以人民币为单位,不能以美元计(即要排除汇率变动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即可计算出2020年我国总共可以排放多少CO2。
我国2005年的GDP总量是18.39万亿元,根据GDP逐年的增长率,2008年的不变价GDP为18.39 × 1.116×1.13×1.096=25.42万亿元(该年的名义GDP为31.40万亿元)。假定到2020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9%、10%,则2020年相对2005年的不变GDP将分别为64.01万亿元、71.50万亿元、79.78万亿元。根据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数据,2005年我国通过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产排放的CO2总共为56.26亿吨,碳排放强度则为56.26/18.39=3.06吨 CO2/万元(RMB)。以2005年的排放强度为基准,我国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将分别降低到1.683(3.06×0.55)至1.836(3.06×0.6)吨CO2/万元(RMB),可排放的CO2总量则增加到107.73(1.683×64.01)至146.48(1.836×79.78)亿吨,以联合国公布的预测人口计算,该年我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将从2005年的4.28吨CO2,增加到7.58(107.73/14.21)至10.31(146.48/14.21)吨CO2。为便于验证,我们将有关数据列于表一、表二。
温总理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曾明确承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这就可以理解为45%的相对减排是我国的最低目标。因此从表二可知,如果我国能保持年均GDP增长率达10%,到2020年可排放的CO2总量为134.27亿吨,比2008年增加90%,人均排放量为9.45吨CO2。我们可以先记住这组数据。
2020年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可达多少?
在总量为107.73亿~146.48亿吨的CO2排放空间约束下,我们可以倒推出2020年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它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化石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例、化石能源本身的结构(即煤、油、气的比例)、水泥生产量。我国2020年的非碳能源目标比例是达到15%,因此化石能源的比例应为85%;今后化石能源中煤、油、气的相对比例如何调整,我国有关部门尚未提出明确目标。我们这里假定保持2008年的比例不变,即煤占75%,油占21%,气占4%;我国水泥生产排放在过去几年中,保持在总排放量的10%多一点。但我国水泥生产量已占全球一半,预期不会有大的增长,这里假定2020年的水泥生产排放同2008年相当,即总共7.23亿吨CO2。在上述假定下,根据表二,在GDP增长8%、9%、10%的情景下,除水泥生产之外的一次能源消费产生的CO2排放总量就分别变为100.50亿~110.29亿吨、113.10亿~124.04亿吨、127.04亿~139.25亿吨。由此,我们可直接计算出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见表三)。比如,在GDP增长8%的情景下,达到2020年减排45%的目标,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的CO2排放系数分别为2.66、2.02、1.47吨CO2/吨(标煤)计算,则给出以下的计算式100.50=(2.66×0.75+2.02×0.21+1.47×0.04)×ET(ET为化石能源总量)。该ET=40.56亿吨标准煤,此值再除以0.85,那么2020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为47.72亿吨标准煤。同样,在GDP增长8%的情景下,单位GDP如减排40%,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则增加到52.36亿吨标准煤。在保持GDP 9%和10%平均增长率的情景下,给出的2020年的一次能源总消费量分别为53.69亿~58.89亿吨、60.32亿~66.11亿吨标准煤(见表三)。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CO2排放总量的刚性约束下,如果化石能源结构发生变化,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会如何变化?从理论上讲,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以及国内天然气产量和进口量的增加,我国降低煤炭在总化石能源中的比例是有较大可能的,但2020年“近在眼前”,此比例变化不会太大。在这里,我们假定石油和天然气各增加3个百分点,煤炭减少6个百分点,则在GDP平均增长率达到8%、9%、10%情景下,一次能源的总消费量分别可达48.80亿~53.55亿吨、54.92亿~60.22亿吨、61.68亿~67.61亿吨标煤,比假定化石能源结构不变情景下增长了2%强。可见,化石能源本身的结构调整对排放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记住第二组数据:如果GDP平均增长10%,相对减排为45%,2020年水泥生产的排放量与2008年相同,并且化石能源的内部结构保持不变,非碳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占15%,那么,我国2020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应在60亿吨标准煤左右,比2008年增长约107%=(60.32/29.1-1)×100%。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可达多大?
何院士在他的文章中,特别强调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问题。为此,我们根据“相对减排”承诺,对不同GDP增长速率下,2009~2020年的能源平均增长率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做了计算,结果列于表四。可以看出,这两个数据都同GDP增长速率相关,增长越快,它们的数值亦越高。我们可以大致给出这样的结论:在GDP增长9%到10%的情景下,到202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应调整到0.6左右。根据有关数据,2000~2008年的平均能源消费系数为0.9。
需要说明的是:何祚庥院士的“担忧”一部分来自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先生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仍将高达44亿吨标煤左右。如以44亿吨标煤为基数,在GDP增长8%~9%的情景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只能在0.39~0.44之间。在何院士看来,要达到如此节能的程度,可能性很小。但从我们前面的计算可知,44亿吨标煤非为“硬约束”,不应作为“担忧”的理由。至于弹性系数届时能否调整到0.6,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何评价CO2排放控制目标完成情况?
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代表我国作的承诺其实是一个“组合式”承诺,主要数据有: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后来定为40%~45%),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但国际上只关心这个“组合承诺”中的CO2排放量(由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产产生)。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十分强调透明度问题,即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相对减排”上也要做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这个要求是不符合“巴厘岛路线图”的,因此没有被写入《哥本哈根协议》,但我国为了凝聚国际共识,主动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同意在自主申报排放清单后,可以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接受一定形式的国际讨论和分析。既然可以公开分析,就必定会涉及到如何证明“相对减排”目标完成情况这一敏感问题。
从前面的计算可以看出,我国在2020年前,并不需要确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即可以排多少CO2,完全取决于GDP的增长速率。GDP增长得越快,可排放的CO2总量也就越大。我们预计,在应对国际讨论与分析过程中,歧见是很容易产生的,它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GDP的统计数据。这本不应是问题,因为我们每年都公布GDP的增长率,数据是现成的。但细究起来,可能会产生三方面问题。一是我国政府公布的GDP数据往往小于各地政府公布数据的加和值,即中央政府要挤“水分”。但现在我国政府提出将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显然需要将任务分解到各个地区或行业。如此一来,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根据其自己统计的GDP数值与能源消费量数值,认为它们已完成了减排目标,而中央政府一挤“水分”,从国家整体评价,变得目标没有完成。二是我们国家经常对GDP数据作出调整,一般是调高过去的数据,今后这样的调高作业是否会在国际上引起非议,将成未知之数。三是我国现有GDP是根据“生产侧”统计的,即将一产、二产、三产的增加值相加而得,这同国际上用“消费侧”统计的通行做法不同。以2009年为例,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GDP数据是33.5万亿元,如果将发改委的报告中的商品零售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相加,GDP总量应在36.5万亿元左右,差别有3万亿元之巨。我们认为,有很大的可能,今后中国统计部门为了同国际接轨,也用“消费侧”作为GDP统计基础,这就可能调高GDP总量,使“相对减排”目标变得更易完成。如果我国统计部门真的这样做了,在国际上引起一些歧见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二是CO2排放的统计数据。其实,统计一个国家的CO2排放总量是件难事。目前,国际上公布的各国CO2排放主要是根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做简单计算而得的,它只需三套数据,一是一国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二是化石能源内部煤、油、气的比例,三是水泥生产量。在计算时,都用国际统一的排放系数加权获得。深究起来,这样的“统一计算”会使发展中国家的CO2排放高于实际排放。比如同样一吨标准煤用于锅炉燃烧,由于设备先进程度不同,燃烧效率也不同,这一吨标煤的“燃尽程度”也将不同。发展中国家由于设备相对落后,燃料并没有充分燃烧,故一部分“该排的CO2”并没有排进大气中。我国目前的煤炭消费量约为30亿吨,不同地区的煤炭质量不同,折合成标煤时就会有很大的统计误差;再加上这30亿吨煤炭被各种方式所利用,不同方式的燃烧效率差别也很大。因此,如何得到“相对精确”的排放量,就变成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本文提出这两个问题,并非要说明在证明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统计方式”上的可操作性,而是要说明对与减排有关的问题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性,获得有公信力的统计数据的重要性。唯其如此,才能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国际争议。
如何正确理解何院士的“担忧”
何祚庥院士认同江泽民同志的观点,即处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的国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而我国在“相对减排”目标确定以后,此系数将大大小于1(0.6),因此引起他对中国会不会走向“半个”工业化的担忧。笔者认为,对这样的担心,我们应予以充分重视。
首先,中国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快速增长是由我国正处在“压缩式”发展这一特殊阶段所驱动的,这是一种内在驱动,不会以人的意志而改变。如果考察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碳排放,对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比如,德国在1947~1957年,其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率平均为9.89%;日本在1960~1970年,增长率平均为11.98%;韩国1976~1996年人均碳排放增长率平均为7.05%。这种增长对应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由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引起。我国1900~2005年的人均累计排放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33%、OECD国家的10.54%、美国的5.16%。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处在快速增长状态,如从2000年到2008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8.9%。正因为是“压缩式”发展以及我国过去排放量很低,我们预期我国今后10~15年的排放还会以较快速度增长,它由大量的公路、铁路、地铁、机场、大坝、港口、城镇住房建设及汽车保有量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所推动。我们通过计算发现,我国到2020年,尽管人均年排放量有可能达到10.31吨CO2,处在同日本2008年的排放相近的水平,但从人均累计排放比较,1900~2020年这120年的排放(197.23吨CO2),只相当于美国1900~1915年这15年的排放,德国1900~1928年的排放,日本1983~2005年的排放,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样的排放同国际人均累计排放相比较,亦只相当于1900~2005年的67.6%。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我国目前已达到世界人均排放水平,而乐观地认为今后不再会有大的排放增长。
其次,从能源禀赋来说,我国化石能源中的煤炭相对充足,而石油和天然气从人均看,储量很小,这就决定我国在非碳能源技术成熟之前,能源消费还将以煤炭为主。而煤炭的CO2排放系数是石油的1.3倍,天然气的1.8倍,意味着我国在使用同样单位能源时,CO2排放量比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要多得多。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20年的人均能源消费,如果今后GDP年平均增长9%,我国又实现了单位GDP减排45%的目标,那么2020年,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将是53.69亿吨标煤(表三),比2009年的31.0亿吨标煤多22.69亿吨,11年中平均增长率为5.12%,这相对于2000~2009年平均9.1%的增长率而言,能源消费增长率需要大幅度降低。再来看人均能源消费,在53.69亿吨标煤总消费中,如果平均到2020年我国14.21亿的预期人口,平均每人的消耗量为3.78吨标煤,这个数字并不大,只有2008年日本(应是最为节能的国家之一)的64.30%,韩国的53.22%,美国的34.82%。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我国所谓的“能源消费”,其实一大部分是为他国生产产品而消费,不是中国人自己消费。从估算碳排放的角度,有不少人做过计算,我国碳排放总量中,约30%出自出口产品,即为他国排放。如果我们用同比例扣除这一块,2020年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只有2.646吨标煤,而美国在2008年仅交通能源消费这一项,就达到每人4.3吨标煤!由此可见,将中国视为高耗能国家及浪费能源国家之荒谬。
还有,我们考察一下“十一五”的节能与CO2排放数据,就会明了节能减排的难度。“十一五”节能20%是作为刚性约束指标提出来的,并被分解到各个省区。陈俊武院士在3月9日《科学时报》文章中指出,4年来的累积节能幅度只有7.4%,而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是12.45%,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分析,这个差别可能由于统计局在普查中“按照通用做法,对2005至2007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也做了相应修订”造成的,但目前看来,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并没有自洽(见表五),2005~2009年的节能幅度应是8.2%,显然离20%的目标有很大距离。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来说,大家关心的并不是节能本身,而是CO2的排放。我国2005年到2008年的CO2排放总量分别为56.26亿、61.03亿、66.06亿、70.50亿吨,这样我们获得每年的单位GDP排放量(见表五)。从此表可计算出,2006、2007、2008年这三年我国累积相对减排幅度为9.5%,比同期6.6%的节能幅度要大。如果2020年相对排放比2005年下降45%,2009~2020年的平均下降幅度应增加到4.1%,难度确实很大。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实现“低碳经济”的可能性。目前,国内学术界、企业界、媒体以及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对建设低碳经济的热情非常高涨,并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坦率地说,笔者对此并不乐观。什么是低碳经济?目前并无严格统一的定义,大家基本上处在各自说各自的状态。根据我们的理解,似乎有三种状况被排在低碳经济之列,一是以绝对的低碳排放为特征的经济,二是碳排放从高值逐渐降低时期的经济,三是低碳技术和低碳生活方式不断推广应用的经济。
对第一种情况,可用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做例子,它们尚没有启动工业化,基础设施亦很落后,基本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它们当然是“低碳经济”,事实上我国几十年前亦是这种经济,但这样的经济绝非人类追求的理想经济。
对第二种情况,可用发达国家做例子,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早已完成,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也已经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通过发展新能源和转移制造业,可逐步减少CO2排放,向“低碳经济”转型。但这样的低碳经济是要打引号的,因为这些国家就排放绝对量来说,还是处在世界各国中的高排放国之列。比如,2008年世界人均CO2排放为4.71吨CO2,而OECD国家的人均为10.91吨CO2。从1990年到2008年,发达国家一直在推动减排,并作了很有吸引力的承诺,但事实上,OECD国家在此期间的年均碳排放增长率为0.85%,须知这个成绩是在它们不断往外转移高排放产业的过程中获得的!如果要计算它们的消费排放,估计它们的总排放还得增加20%以上。所以,第二种状况下的低碳经济只是口号上的“低碳经济”,或干脆名之为“忽悠型低碳经济”。
对第三种情况该怎么看?可以想见,随着技术的进步,低碳技术的应用将会增加,但对一个国家的碳排放会有何种影响,尚难预料。如果从发达国家过去20年走过的路看,CO2减排是很难的;此外,对低碳技术,还得计算“全生命周期排放”,比如太阳能设备生产过程本身是高排放过程,这些设备应用10年减少的碳排放,未必抵消得了生产设备过程的排放!在10年的时间尺度上,我国想通过大量生产和安装低碳发电设备而达到CO2减排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即使我国超强度推行这些技术,也不能在2020年前从实质上改变我国还将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现实;至于低碳生活方式,我们当然要大力提倡,但不要寄予太大希望,人性的本质就是不断追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更何况开着私家车上下班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是没有任何道德力量去要求芸芸众生都去骑自行车的!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想见,我国只能建设第三种状况的低碳经济,并将面临一个“逻辑困境”,即一面碳排放快速增长,一面说正在发展低碳经济。所以,我们要充分重视何院士的“担忧”。
最后,给出几点评论性看法,不算结论。
1. 到2020年,我国通过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产排放的CO2,以单位GDP计,比2005年减少40%~45%,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如果没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将非常大。但我们并不认为由于我国承诺了如此高标准的相对减排,中国的工业化会停在半途。
2. 在管理上,我们还停留在将节能作为约束性指标的阶段,从执行国际协议看,我们需尽快转到以排放(包括CO2、SO2、COD、大气粉尘等,尤其是CO2)为约束性指标的新阶段。但如何尽快将国家级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并形成一套严密的考核指标,还有不少挑战性的问题要研究和解决,包括如何对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进行碳排放计量,如何制定各个行业的碳排放标准,是否需要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如何制定与排放有关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碳排放问题上,发达国家的理解比我国要深入得多,我们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是被“碳减排”的国际洪流“挟裹”着前进的。现在,我们需要重温毛主席的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3. 在国家层面上,数据统计是个大问题。我们在本文中强调这一点,丝毫没有统计数据有“做手脚”的空间的意思,而是强调在统计数据产生过程中,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仅凭统计部门,有可能会产生自相矛盾的结果,从而不必要地引起对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怀疑。
4. 对低碳经济的宣传要谨慎。从历史和现实看,低碳经济确实有,最不发达国家即是,而“低碳发展”的国家迄今尚未出现,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亦不会出现。在低碳技术投资效益不高的限制下,把大量资金投入其中,实非谋国之道。从现阶段看,还是要通过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来谋划未来真正的低碳经济。
5. CO2减排最终还会归结到能源利用上。从我们国家看,煤的清洁利用应是重中之重,水电和核电亦要加快建设,另外我国天然气,包括页岩气的开采还有很大潜力,亦应加快勘探、开采和利用,这些都是减少CO2排放的主要手段,同时还可保证满足我国对能源快速增长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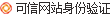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