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呼应最近人民网上的一篇报道,及今年3月《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人民网的报道题为《四位科技界知名人士建言下决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详见: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444910.html;《光明日报》的文章详见:http://www.gmw.cn/content/2010-03/10/content_1069204.htm。)
两年前,清华大学化生基科班的毕业生请我留言。我绞尽脑汁,想出一句代表了自己很多想法的话: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
做学问必须诚实,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两方面。首先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诚实作研究的前提下,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至错误是很常见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可以说,许多学术论文的分析、结论和讨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这种学术问题的争论往往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是前沿的科学研究,越容易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1938年,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获得诺贝尔奖。其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现了第93号元素。实际上,尽管费米在1934年曾报道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可以产生第93号元素,但德国化学家哈恩在1939年1月发表论文,证明产生的元素根本不是93号元素,而是56号元素钡!但这个错误并没有改变费米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事实,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在学术上的进取。费米很快提出后来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链式反应理论,并于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再举两个生命科学界的例子。因为发现蛋白质的磷酸化,美国生物化学家爱德蒙德·费舍尔(Edmond Fischer)和艾德温·柯瑞伯(Edwin Krebs)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如果仔细阅读他们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几篇关键学术论文,你会发现他们当时对不少具体实验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一定差距,用今天的标准可以说不完全正确。然而,瑕不掩瑜,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最优秀最有创意的突破。美国生物化学家托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是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其获奖的工作主要是2000年发表于《科学》周刊的两篇文章。文章阐述了核糖体大亚基的晶体结构及蛋白质的肽键形成机理,这是结构生物学的精华展示。但大家也许早已遗忘,施泰茨那两篇文章发表不久,《科学》周刊就在2001年初刊登了两篇技术评论的文章,质疑施泰茨提出的肽键形成机理。说白了,有人认为施泰茨提出的机理是错误的。
举这些例子是希望大家区分误差(error)与造假(fabrication)的区别。比如一个实验由于条件有限,作出了一个结论,后来别人用更先进合理的实验手段、更丰富的实验数据推翻了这个结论或对这一结论作了重要修正,那么第一篇文章只要详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验条件,就不能被称为错误,更不是造假,也无须撤稿。但如果明知实验证据不足,为了支持某个假设的结论而编造实验条件或实验证据,这就是造假了,视为学术不端(scientific misconduct)。
但诚实的学问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作出了相应的贡献(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后,才应该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署名。这一点,很多人作不到。即便在美国,偶尔也会出现大老板强势署名的事情。在国内,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利用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一些年轻学者不得不在文章里挂上自己的名字,有时还以许诺未来的科研基金来换取论文署名。其实,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学术道德,对整个学术界风气的影响更为恶劣。
做人也要诚实,但更重要的是正直
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撒过谎,也不相信成年人的每句话都是完全真实的;很多特定环境下善意的谎言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得到大家的赞同;比如对危重病人的病情的适当隐瞒。但一个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一辈子正直!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而言,必须邪不压正。社会风气需要正直,学术风气更需要正直!
我小时候,性格好强。长大以后,也常常桀骜不驯。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难以容忍做人的不正直。讲个有点离谱的故事:我从小觉得尊老爱幼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深恶痛绝。1988年我读大三,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因为一个小伙子不肯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又不听我的好言相劝,我只好动手,强行把他赶到了他该站的地方。在我看来,这位小伙子做人行事不够正直。
全职回国两年半了,心里最大的不快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有些学生)对是非曲直看着于己无关便无动于衷,这让我非常忍受不了。每次看到媒体报道见死不救、袖手旁观时,我都禁不住想问一下旁观者:如果哪天你成了受害者(victim)怎么办?后来一想:大概旁观者都觉得轮不到自己,侥幸罢了。
在学术界,正直可以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国内盛行的学术潜规则是造成学术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其危害不亚于学术造假。不同的是,学术造假很容易被发现,而潜规则虽然无处不在却很难人赃俱获。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这些学术潜规则都是与正直的学术道德背道而驰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人声讨潜规则,同时相当一批人又千方百计地适应、应用潜规则,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最大的学术潜规则是“官商勾结”。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却切中时弊。它来自一位科技界领导。2008年参加某个部门的小型研讨会,我发言陈述科研基金申请中潜规则的危害。我的话音未落,这位领导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施教授,看来你还是太幼稚,低估了国内的潜规则:现在说白了就是官商勾结。”
我很意外,反问道:“怎么讲?”
“官,就是我们这些有实权的局、处级领导,手握行政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确定顾问组成员和专家组组长人选。商,就是与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款科学家,他们手握立项、评审大权,常常可以掌握几亿、十几亿的科研经费,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审结果。”
“怎么勾结呢?”
“很简单。商有求于官,因为他们需要这种权力,既可以为其本单位带来利益,又可以利用巨大的资源来党同伐异。而官也有求于商,不仅商的赞美之词可以转化为官的政绩,官还可以从商那里拿到直接的好处……”
学术界的潜规则在实质上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大家都知道它的不对,为什么不能一起自觉地抵制这些潜规则呢?
回国两年多来,我数次申请过科研项目的基金,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评委事先沟通过。我也参加过多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从来没有向这些科研项目的任何一个申请人事先沟通过情况。这本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然而,这些职业道德操守却被我们的潜规则冲得七零八落。最后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一次参加某个重大项目的评审,周六下午我才接到通知,可周日上午手机就收到6个陌生人(我确定从未给他们留过电话号码)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作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等。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职业道德,各行各业也应当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后记
其实,这篇文章几个月之前就已写好。写的时候,字斟句酌,深怕言过其实,希望只针对现象,不希望涉及到任何个人或任何部门。即便如此,成稿之后,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公开发表。如果发表出来,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憎恨,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但如果不说出来,则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自己回国的目的,更对不起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师长、同事、朋友和学生。衷心希望这篇对事不对人的文章能起到一点促进科技体制改善的目的。从我做起,用我们每个人的自律与职业操守来促进大环境的逐渐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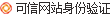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