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匮乏是我们民族从事原始性创新的软肋。有必要重新认识科学精神和科学精神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各项事业均取得重大进步,科学技术领域的面貌也取得伟大的变化。但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还从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作为上述现象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中国极度缺乏世界级的自然科学大师。去年,钱学森老人逝世了。温家宝总理多次引用钱老生前的话,引发了社会热议“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温总理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温总理2009年教师节看望教师时的讲话。)
显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和深刻的。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对此有过一些探讨和论述。观点深刻和言辞激烈的代表当属学者袁绪程在其博客中发表的《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一文。这篇博文认为:不可能存在没有伟大人物的伟大时代,也不存在缺乏大师的伟大复兴。中国必须期待一大批学术大师的产生,否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袁同时为中国重建“学术大师”的生态环境开出了如下药方:狠抓教育、善待人才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近日重读《科学的历程》(吴国盛,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史纲》(柏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及施尔畏博士的新书《观察与思考》(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感慨良多。我认为:现代科学精神的匮乏乃是我们民族缺乏科学大师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让我们从科学精神的起源、科学大师成长的个人经历以及大师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探讨原始性重大创新所需要的基本个人素质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的特征。
科学精神起源于好奇、闲暇和自由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家的气质及行为规范等精神层面的反映。科学精神有多方面的内涵,其中:热爱真理、理性与实证、怀疑与批判、自由主义和协作意识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
众所公认,以逻辑严谨、追求实证、还原自然过程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精神起源于古希腊。在这个伟大时代,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众多宗师大家。有最早期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有人文科学家苏格拉底,体系哲学家柏拉图,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默东、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得,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等等。
科学精神之所以起源于古希腊,固然是由于其继承和光大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希腊的奴隶制和城邦民主制为科学精神的诞生提供了物质条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篇就说:科学和哲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一是对自然界的惊异而产生的好奇心,二是有思考这些好奇心的闲暇时间,三是有不受束缚的思想自由。
希腊人天性乐观,热爱生活,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是他们欢乐生活的写照。他们崇尚理性、热爱真理,对知识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充分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寻找世界本源的执着追求和热爱。希腊的奴隶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的优裕生活,使得民族中的精英个体得以闲暇并思考世界的本源问题。希腊民主的城邦制有助于科学和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由于各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同时,没有任何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来束缚人们的头脑,即或是体现希腊宗教思想的希腊神话,其完备的诸神谱系也反映了希腊宗教思想的对象性和逻辑性;所有这些,使得整个希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从科学精神的起源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真理的热爱、允许自由探求的物质条件和思想环境是科学精神萌芽的三大基本要素。
在伟大的希腊科学精神的影响下,希腊产生了许多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直到公元5世纪前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以柏拉图学园被封和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为标志,欧洲进入了长达5个世纪的黑暗年代。从11世纪开始,基督徒带着一种狂热的宗教情绪开始了延续20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运动促成了拜占庭所保留的希腊文明和欧洲人所继承的罗马文明的交流融合。同时也将阿拉伯人先进的科学、中国人的四大发明等带回了欧洲。12世纪,欧洲掀起了翻译阿拉伯文献的热潮。希腊原始文献经叙利亚文到阿拉伯文再被翻译成拉丁文。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科学著作,开始为欧洲人所熟悉。在这次欧洲学术复兴的过程中,诞生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培根主张靠“实验来弄懂自然科学、医药、炼金术和地下天上的一切事物”,这一思想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科学大发展的基石。
当代科学已经具有了若干新的时代特征。但我仍然相信,回顾科学的萌芽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本质。
非功利性是科学大师个人成长的必要条件
非功利性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基本属性之一,功利主义对科学精神的所有要素造成直接伤害。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对真理的热爱;对功利的追求会诱惑我们减少必要的认知成本,进而损害理性实证的复杂过程;对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们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从于权威和权贵;最后,对功利的追求必然从根本上不利于团队的合作。有学者认为:需求驱动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社会层面看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对于科学家个人来讲,对物质性功利的过分追求必然有碍于其原始性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应该看到的是:丰厚的物质基础可能是减少科学家物质性功利追求过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观世界科学发展历史,除了极个别的天才,几乎所有影响人类进程的科学大师都无一例外地拥有良好的家庭物质条件。这个结论可以在美国应用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天文学博士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得到佐证。良好的家庭物质条件(当然还有其他的教育条件),使这些大师从童年时代就有可能受到较弱化的功利主义影响,从而使得科学成为他们更加纯粹地认知自然实践而不是或不完全是谋生的手段。古希腊时期的科学哲学巨匠也基本上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如西方第一个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泰勒斯出身于带有腓尼基人血统的贵族;柏拉图的母亲是雅典执政官七贤之一梭伦的后裔,父系可以追溯到古雅典王卡德鲁斯;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各马克是马其顿王的御医;科学巨匠阿基米德是意大利西西里岛叙拉古国王的亲戚。
在近代科学大师中,达尔文也许是不以科学为谋生手段的典型。他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在青少年时代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爱因斯坦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和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合开了一个为电站和照明系统生产电机、弧光灯和电工仪表的电器工厂。母亲玻琳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妇女,非常喜欢音乐,在爱因斯坦6岁时就教他拉小提琴。显然,他的童年也没有感受到太多生存和谋生的压力。有朋友曾提出反证,说费米是贫苦农民出身。仔细查阅资料发现:费米确实在乡下度过了两年的童年时光。他的爷爷斯德法诺在费米家族中第一个放弃耕地并投身效力于巴尔马克公爵,在费米的传家宝中,还保留着斯德法诺当年穿的制服上的铜扣子,上面有那位公爵的名字和邦徽的浮雕。他的父亲亚贝托在铁路局做职员,41岁时和比他小14岁的小学教员伊达·第·嘉蒂丝结婚。费米是他们连续三年生育的第三个孩子。这使他母亲没有工夫照料这第三个孩子,只好把他送到乡下,交给奶娘抚养,直到两岁半以后才抱回家来。可见费米也非出生于一般的贫民家庭。虽然肯定会有例外,但我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早期家庭环境对形成孩子的世界观至关重要,并因此而影响着学术大师诞生的过程。
由于科学精神所要求的非功利性主旨,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科学研究不应该更多地成为科学家谋生的手段,而应该更多地成为满足科学家好奇心的认知实践。自然基础科学工作者一旦背上沉重的谋生包袱,其对真理的热爱将有可能让位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中国由于长期的贫困,以及清朝末年所见识的坚船利炮的西方科技威力,使得国人对科学的功利有崇拜般的痴迷,而对孕育现代科学的科学精神始终不以为然。如清朝末年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中华民族面对科学的基本心态的写照。“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试图在保持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建设一个近代的工业社会,其结果必然失败。五四运动的先驱严复对中国文化求真精神的薄弱十分焦虑,在所翻译的《群己权界论》一书的“译凡例”中指出:“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群己权界论》,英国约翰·穆勒著,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竺可桢在1935年的一次《利害与是非》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近30年来所提倡的科学救国,只看重西方科学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却忽略了培养科学成果的科学精神,认为科学精神应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真正阻碍中国科学精神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至上和实用思维。我们认为:对待科学的功利主义思想,除了文化传统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长期积贫积弱的社会发展造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兼容并蓄的社会思想环境是科学昌盛、大师频现的另一重要基础
近代科学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首先是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精神,认为人乃万物之本。就像莎士比亚所赞叹的:“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人文主义所推崇的理性精神,正是科学精神的基本支柱。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路德新教所宣称的“因信称义”,表达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颠覆了教会的绝对统治权威。长期以来,被神恩、天启、权威所禁锢的人类思想开始得到解放。
在这一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宗教和科学发展的关系。哥白尼的卫道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布鲁诺,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教廷处以火刑,但哥白尼本人却是一个职业牧师。正是在长期的职业宗教生涯中,他利用业余时间创立了伟大的“日心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在近现代科学史当中,不乏自然科学大师出身于宗教信徒,在修道院任职的孟德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长达12年的豌豆杂交试验,以遗传定律奠定了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础。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路德新教所宣称的“因信称义”,是基督教思想方法中归于理性的表现,而这种理性的思维无疑有利于现代科学的产生;二是新教具有宽厚平和的特性。例如:近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因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教会判处终身监禁。他一直被监视居住在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幢别墅里。正是在这里,他又完成了另一部伟大著作《两门新科学》,并最终得以出版。1980年,教廷正式宣布对伽利略的判决是不公正的,稍晚些,受火刑的布鲁诺也被教廷平反。
至于现代西方科学家当中,基督教的信徒同样比比皆是。1980年,包括杨振宁、丁肇中在内的7名诺奖获得者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使命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科学,这个曾经的神学的“婢女”已经可以和“小姐”坐而论道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宗教接受理性的时候,科学就没有了最后的思想羁绊,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来源于思想的自由。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得到了不可遏制的发展!“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国际歌》里的歌词,永远都不会过时。
关于现代科学何以未产生于中国以及为何不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已经有太多的研究,如李约瑟难题等等。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明了科学精神产生的基础,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科学大师不断诞生的条件,并应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力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科学史研究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兆期,但随后都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而趋于消亡和失败。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周、汉两朝,也分别经历过西东两周、西东两汉的动乱过渡时期。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的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在其289年的存续时期内,也发生了无数的内外战争、宫廷变乱、藩镇割据等等重大社会动荡。这些,都摧毁了原本微薄的社会物质基础。此外,中华民族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生存压力特别巨大。因此,必须着力推进政治改革,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发展经济,筑牢物质基础,藏富于民,着力蓄养一大批富足生活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跨代长期存在,应该是滋养学术思想大师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先导。史学家公认:周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而在汉帝国的鼎盛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汉民族思想的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如同修筑长城永远不可能真正抵御外族入侵,大一统的封闭思想体系也不可能长期地富国强民。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要防止学术的官僚化,弱化以院士制度为代表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官僚体系,在法律的框架内,以更加相信群众的心态,欢迎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三,在自然基础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设计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义色彩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科技界,仍然秉持“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中,最广受诟病的话题是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管理。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我爱真理、我更爱论文”的不良学术氛围,和“我爱真理、但我不能得罪学术权贵”的处世价值。因此,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应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改进评估方法、减少评估频度并进而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
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的民族,也是聪颖智慧的民族。我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积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同时也随着中华民族对现代科学精神的不断揣摩、理解和实践,我国必将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巨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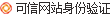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