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能源消费量也随之快步攀升。数据显示,当前我国GDP占世界的7%,能源消费却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7.7%。显然,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将受到能源资源尤其是环境的严重制约。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推动世界向低碳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将进一步向节能、高效、清洁、低碳方向转变,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在调整能源战略。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将2010~2050年作为能源体系的转型期,在此期间,能源体系要从目前的粗放、低效、高排放、欠安全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型为节约、高效、清洁、多元、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其中2010~2030年被定义为转型期中的攻坚期,而2010~2020年,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更是转型的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在整个能源体系转型期内,即使考虑到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均得到极大发展,煤炭也仍将在我国能源供应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是中国式低碳经济的关键。
多年来,倪维斗一直在为推进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与多联产相结合的煤炭清洁利用技术而积极奔走,他认为,“IGCC+多联产”符合中国煤炭资源丰富的国情,且发展潜力巨大。
在他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积极推动下,我国首座IGCC示范工程项目——华能天津IGCC示范电站于2009年7月6日正式开工。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洁净煤发电技术的发展、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以煤为主”不容回避
从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一直占据比较大的比重。根据国家能源局2009年公布的数据,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68.7%,远高于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根据中国工程院《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的数据,在对可再生能源、核电、天然气、石油需求作比较乐观估计的情况下,到205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构成中仍将占有40%的比例,而年煤炭需求量不会低于25亿吨标准煤。这意味着,在2010~2050年我国能源体系转型期内,累计消耗的煤炭总量将达到1000亿吨标准煤。
“在近30~40年内,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中无法改变以煤为主的现实。”倪维斗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演讲中也表示,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根据我国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对各个阶段能耗总量控制设定的目标为:到2020年实现能源消费总量为40亿吨标准煤,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5亿吨标准煤,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50亿~55亿吨标准煤。显然,要想实现这3个阶段能耗总量的控制目标,如何打好“煤炭牌”是关键。
在今年6月举行的中国能源战略与“十二五”能源发展论坛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也表示,应结合当前背景,转变能源战略理念,促进煤炭的绿色生产和清洁利用。
IGCC“后劲”足
从发电的角度看,目前国内煤炭清洁利用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超临界、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这种技术旨在让煤更有效率地燃烧,产生温度更高的蒸汽和压力。蒸汽被用来推动涡轮发电。该技术对污染物采取的是“尾部处理”的治理方式,即通过安装脱硫、脱尘及脱硝等设施实现排放达标。
另一个方向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即IGCC)。与上述技术不同的是,IGCC采取的是先治理后发电的污染物控制策略,即先将煤进行气化处理,把气态煤中的污染物脱除后再燃烧发电。因此,IGCC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和汞等污染物的排放。
倪维斗告诉记者,从国内的应用情况来看,超临界、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比较成熟,成本也比IGCC更低,是目前的主流技术,但“这种形式并非一成不变”。
据倪维斗介绍,欧洲从1998年就启动了AD700(蒸汽参数达37.5MPa,700℃/720℃的先进超临界燃煤电厂技术)计划,预计运行温度将提高到700摄氏度,压力将提高到375个大气压。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仍有许多技术问题尚未解决。
“最主要的就是材料的问题。运行温度提高后,锅炉的过热器材料及管道需要采用更耐热的镍基合金,落实到每一个千瓦数的成本会很高。”倪维斗说。而由于超临界燃煤技术采用“尾部处理”的治理方式,在未来对排放物控制愈加严格的情况之下,该项技术的排放物治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此外,超临界燃煤技术在烟囱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浓度和压力都比较低,这也为碳捕获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就目前的超临界燃煤技术而言,想要进行二氧化碳捕获的话,成本至少要翻一番,发电效率要降低11个百分点,如果原来是44%,二氧化碳脱除后变成33%了。”倪维斗说。
与超临界燃煤技术相比,IGCC采取的则是先治理、后发电的污染物控制策略。对二氧化碳,可以在燃烧以前、在高浓度高压力条件下将其脱除。
“当然,IGCC的二氧化碳脱除也需要一定的效率降低的代价,但比‘尾部处理’方式的成本要低一些,对发电效率的影响也比较小,降低6~7个百分点。这是IGCC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比较大的优势所在。”倪维斗说。
倪维斗告诉记者,目前IGCC的初期投入相对较高,发电成本是普通发电成本的1.5~2倍。但煤在气化之后的用途非常广泛,比如做化工原料,或是合成高附加值的燃料等,如果把发电和多联产进行耦合,统一考量,对物质流、能量流加以优化,那么投资的整体效益也会得到提高。
“与超临界燃煤技术相比,IGCC在发电效率方面相对来说有更大提升空间,在污染物治理、脱碳方面也有独特优势,还能通过和多联产耦合降低建设成本,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倪维斗总结说。
“三个五年”的战略思考
虽然IGCC多联产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该项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却较为缓慢。倪维斗告诉记者,发展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电和化工行业结合的思想阻力比较大,二是相关部门对IGCC的一些偏见,从而持过度谨慎的态度。
不过,在倪维斗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积极倡导下,我国首个IGCC示范工程项目——华能天津IGCC示范电站已于2009年7月6日开工。对IGCC和多联产的认识,尤其在国家层面已经见到可喜的变化,观念上也有所“松动”。
据了解,工程第一阶段的规划是建设一台25万千瓦等级的IGCC发电机组,机组采用华能自主研发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000吨/天级两段式干煤粉气化炉。首台机组计划于2011年建成。据华能天津公布的数据,该示范电站建成后,发电效率可达42%,脱硫效率达99%以上,可回收高纯度的硫元素,并将氮氧化物的排放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倪维斗表示,该项工程在气化炉的自主研发,净化装置、发电装置的整体控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探索价值。
记者还了解到,在倪维斗的积极努力下,他所倡导的IGCC多联产已被写入《新兴能源产业规划》及“十二五”期间的能源发展规划当中。
对于IGCC多联产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倪维斗认为示范工程太少,国家应再批3~5个试点,同时采取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互相的对比和学习,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他还向记者阐述了自己“三个五年”的战略思考:“比较理想的状态是,2011~2015年,也就是‘十二五’期间,能够建成3~5个示范项目,积累经验;‘十三五’期间开始进行小规模推广;2020年以后,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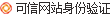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