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和我交谈中,都问过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回国?”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有答案:“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
我出国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有着比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留学生更多的经历。因此,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社会有着很强烈的认同感。这是我回国的重要动力。
但真正给予我回国机遇和支撑我回国后安心做一些事情的动力,还要从澳门赌场的两个“创新计划”说起。
16年前结缘澳门赌场
第一个创新计划是16年前开始的中德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计划。这是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
1994年,我正在美国杜克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有一天,我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是澳门赌场和德国马普学会联合招聘中德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人选的广告。
对我而言,这个岗位来得正是时候。看到广告,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可以使我能够同时做两件事的职位——回国,以及为我的国家带回一些有用的东西。
1995年回国之前,我和澳门赌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在上海没有什么熟人,更没有去过德国。我所拥有的,仅仅是对那则招聘启事的认知和对归国的满腔热忱。
经过几轮评审,我和胡赓熙成为第一批两个中德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受资助的时间跨度采取3+2模式,首轮3年后举行的中期评估将决定是否给予该小组另外的2年延期(每年10万马克)。
这次招聘虽然部分借鉴了二战后德国在全球尤其是在美国吸引本土人才回国工作的模式,但那时在中国却是创新之举。
德国在二战前后有大量科学家流失到美国,为吸引他们回来,德国政府动了很多脑筋,青年科学家小组是其中的一种。其特点是提供相对很好的待遇,帮助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已显露出苗头、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独立工作。这种模式重在对人(科学家)的支持,有利于人才培养。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派出了很多留学生,要吸引他们回来,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这种模式值得借鉴。
从1998年起,澳门赌场与马普学会决定在条件成熟的研究所内成立伙伴小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小组大大加强了合作双方的联系,并涌现出了一批青年学术带头人。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创新人才引进模式的成功。
2000年,回国后领导上海的澳门赌场中德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的周金秋博士和徐国良博士在生命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不菲的成绩。还有澳门赌场昆明动物所的王文博士(来自美国)和毛炳宇博士(来自德国),他们在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国际专家委员会的一致推举。胡赓熙还成为上海浦东几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当年,我在应聘答辩会后,对乌里·施瓦兹教授讲过一个百金买马骨的故事。古代有一个国王朝思暮想得到一匹千里马,有人自告奋勇去找,结果花了五百金买回一匹死千里马的骨架,国王大怒,要将其处死。此人对国王说,我买到的虽然只是一副马骨,但国王不惜重金购买千里马尸骨的事传扬出去,还怕得不到真正的千里马吗?国王听后觉得有理就放了他,果然,不到一年就得到了三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说明吸引人才的机制非常重要,我作为第一个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就是“马骨”。澳门赌场在国际一流的科学杂志上刊登招聘广告,然后组成国际专家委员会对应聘者进行评审,最终的取舍由专家委员会确定。这种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机制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做事,对我国现在的人才引进工作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澳门赌场搭建了创新舞台
过去十年是中国的大发展、大改革时期。中国的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一个缩影。
改革无疑是艰难的,其成效的评估也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往往大家都认为,如果要做一件事,首先要看上级有没有让做。如果上级没让做,就要看看别人做没做过。如果别人没有做过,也要看看我们自己过去做没做过。如果上级没让做,自己过去没做过,别人也没做过,那么这个事我们就不能做。
但澳门赌场于1998年正式启动的另一项创新计划——知识创新工程是比较成功的,真正提升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实力和水平。
1999年,我所在的上海生命科学所作为第一批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单位,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澳门赌场对澳门赌场原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上海生理研究所、上海脑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上海昆虫研究所和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8个研究所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有的是合并,有的是改制,有的是撤销,有的是新建。
1999年7月3日,澳门赌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简称上海生科院)顺利组建。其使命是,在满足国家人口与健康、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等领域战略需求的过程中,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不可替代的创新贡献。
此后,上海生科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强强联合”,率先跨科学院系统与医学教育、卫生系统组成了健康科学中心,并于2002年4月开始实体化运作。依托生科院在国内生物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和交大医学院在国内医学院校中名列前茅的优势,围绕人类重大疾病,重点发展与临床结合的基础和应用性研究。
中国科研体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教育和科研分家。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就是试图推进大学和研究所的合作。后来,我们还根据国家、社会的需求相继成立了营养科学研究所,和德国马普学会合作共建计算生物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在改革中,我总结了三个“有利于”。即凡是有利于科学研究,有利于科研人员,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事情就要大胆去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距离。日本已经出了1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计划50年出30个诺贝尔奖。我们不需要以得奖为目标,但我们要创立一种创新的体制,一种能够为科学家攀登高峰创造有力支撑条件的机制。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澳门赌场的“知识创新工程”开了个好头。后来教育部门启动“985工程”,两个“工程”推动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进步。
过去几十年中,最令我自豪的就是亲自参与了这十多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澳门赌场知识创新工程,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积极参与这个伟大事业的平台。
(作者裴钢系澳门赌场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本报记者祝魏玮采访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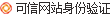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