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我就不能不想到我念高一的母校――江西九江的同文中学。2009年应《光明日报》“母校礼赞”专栏之约,我写了一篇《读好书 做好人》稿,5月13日发表。之所以用这个题目,因为这是同文中学的校训。同文中学诞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之时,历经中华民族百余年苦难风雨,与民族同患难,与国家共呼吸,正如今天同文中学校园十数株150年以上树龄的香樟一样,根固于地,擎天而立,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读好书 做好人”的校训真好,既可以理解为:要读好的书,要做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要把书读好,要把人做好。不论如何理解,都可归结为:读书,要有益于身心健康;做人,要有益于国家、民族;读好书是为了做好人,做好人就要求读好书。这个校训把为什么读书、如何读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讲得简扼而深刻。笛卡尔讲得形象:“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991年,我增选为澳门赌场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那是1980年后的11年间澳门赌场第一次增选,备受社会关注。当时很多记者采访我,向我提了很多问题。问题之一是:“哪一本书给你印象最深,对你影响最大?”我想了想,就讲:“无可奉告!”我真的讲不清是哪一本书起了其他书不可比拟的作用。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日积月累的,是潜移默化的,是会从量变到质变的。但在记者一再提问下,我就讲了:如果只凭直接的印象来判断,有两本,都是解放初期读的。一本是小说,奥特斯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哲学,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前者给了我巨大的长期的鼓励,直面人生;后者给了我深刻的初步的启迪,认识世界。小说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精力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在1963年读到雷锋同志所讲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两者多么契合!讲法似不同,本质、境界全一致!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引导着我。《大众哲学》讲“量变到质变”这一规律用的是西湖雷峰塔为什么倒塌的实例,指出抽走导致塔倒塌的最后一块砖时,就导致了质变。当时,我就想到了我国古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两本书,使当时解放初期还只十六七岁的我下决心跟着共产党,对献身共产主义崇高的事业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很快,1950年1月我就入了团,1956年2月我就入了党,无论是百花争艳的春天、天高气爽的秋季,还是暑气逼人的盛夏、天寒地冻的严冬,无论是身处顺境逆境,我抚心无愧,从未对自己的坚定信念有所动摇。
如果深究我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深,我从4岁到9岁,就是在学习传统文化中度过的。特别是《论语》对我自幼深深的熏陶。其实,《论语》中的词汇、语句、论述、思维等等早已深入了我国人民生活与思想之中,从“启发”、“反省”到“温故知新”、“后生可畏”,到“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君子不器”、“和而不同”,如此种种,何能胜数。在思考问题或感情沸起时,幼时所受的这些教育内容就自然会在其中。所以,在我接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工作后,又一次读了《论语》,后来,至少有10次以上,用《重读〈论语〉――兼谈如何读书》为题,作了系统的演讲,实质上,是汇报我个人读书,特别是读《论语》的内心体会。演讲中我谈了四点体会:一、读书,就要把握整体地读,以孔解孔,这就防止理解走偏。例如,“学而时习”这个“习”字,主要是“实践”的意义,而孔子所讲的“学”不仅是指向“书本”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实践”学,在“实践”中学。二、读书,要抓住重点地读。一本书是个整体,但其中会有主有次,应当抓住重点。《论语》的重点有二:一是“仁”,一是“学”。“仁”是孔子希求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而“学”是达到此一境界的道路。当然,再深入下去,孔子学说的精髓是“中”、“中道”、“中行”、“中庸”,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诚信。《论语》中的“忠”主要涵义是“诚”。三、读书,要下学上达地读。一本书,一篇文,一段话,它的论述往往是针对在当时条件下具体的事情,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读者还应抽象到形而上的层面上去理解。《论语》讲治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就可理解为:各应在其位,各应谋其政。四、读书,要联系实际地读。读书,我不赞成统统要“立竿见影”,社会急需的而自己又能做的当然就尽快尽力去做。日本近代著名的企业风云人物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人誉之为日“企业之父”、日“金融之王”、日“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他总结办企业成功经验的书,题为《〈论语〉加算盘》。《论语》喻义、文化,算盘喻利、经济,他办企业成功之本就是将义与利、文化与经济、士魂与商才紧密结合起来。他讲:“有士魂尚需有商才,无商才会招来灭亡之运,舍道德之商才根本不是商才,商才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因此,论道德之《论语》自应成为培养商才之圭臬。”“以《论语》为处世之金科玉律,经常铭之座右而不离。”《论语》对商场尚且如此,对社会其他方面的重要性更可想而知!
我校涂又光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冯先生逝世后的遗稿,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均由涂先生定稿。涂先生常讲:“在基督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古兰经》。我们中国呢?我看至少知识分子至少要读两本书,《老子》、《论语》。”后来,我看到任继愈先生也有类似的讲法。正因为如此,我任校长后,硬是挤时间熟读熟背了《老子》,受益匪浅。读《老子》,以老解老,我读出了什么?讲得概括一点,就是“自然、无为”四个字,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一文或许是对《老子》一个很好的诠释。当然,这四个字远不能包括《老子》的全部内容。“自然、无为”,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一切应全面而协调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柳宗元讲得很形象、很深刻:“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就成功;而“好烦其令,而卒以祸”,就失败。
深究我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其次是革命传统文化、革命经典一直伴着我从十六七岁走到今天将跨入八十岁了。我坚决跟着共产党、献身崇高事业的理想就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开始的。我读过一本德国小说,叫《第一步》,讲的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德国有一批青年,他们各自经过哪件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对我而言,这个“第一步”,是1949年5月23日在南昌迎接解放,看到解放军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情景,这同国民党的兵特别是伤兵到处横行霸道、欺辱群众的情景截然对立,是这个对立的现实;这个“第一步”,之后能够深入,能够坚定,能够持续,就是以上两本书奠的基。当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从1951年读第一卷到1960年读第四卷,到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印象当然深,影响当然大,特别是其中有许多文章、许多论点、许多警句尤为如此。例如“老三篇”:《为人民服务》讲的是人生价值或人生意义的取向;《纪念白求恩》讲的是责任感;《愚公移山》讲的是行为准则。对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给我人生奠了基,那么,革命传统文化、革命经典不仅在强化着这个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我人生导了向。什么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我读《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为什么感觉那么亲切,就因为它们是中国化的,即中华民族文化化了的、中国实际化了的。
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人能从动物人变成社会人,从野蛮人进步为文明人,从低级文明人发展为高级文明人,靠的就是文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一切的创新都是从文化创新开始的,而一切文化的创新又是从知识创新开始的。文化的载体是知识,知识的载体至今主要仍是书本。高尔基有句话讲得很深刻:“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莎士比亚讲得很生动:“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知识是重要的。西方哲学家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言不十分确切。如从反面讲,“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这就确切了。没有知识这一载体,哪里还有文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里的学习,首先就是学习知识,当然不只是学习知识。知识承载了文化,即不仅承载知识本身,而且承载了文化应有的内涵。鹿善继在《四书说约》中讲得很对:“读有字的书,却要识没字理。”读以字表达的知识,但是通过知识去理解没有以字表达的知识所承载的“理”,即文化内涵,首先是思维与方法。知识是文化的载体,而思维是文化的关键,方法是文化的根本。没有思维的知识是僵死的知识,一个高级的书呆子,就像一本大辞典,内容浩瀚,但创造不出任何新的知识。人若如此,他只会照章办事,纸上谈兵,一害他人,二害自己。郭沫若深刻地指出:“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关键在于有思维,这就是“人为万物之灵”之本质。有了思维,知识才活了,能够发展,能够创新,能够超越自己。文化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基因,就在于文化的精神──它不断追求文化本身更深刻、更普适、更永恒,或者讲,更加求真、务善、完美、创新。因此,读书需要对已有的文化理解、领悟,进一步反思、怀疑、批判,而后发展。不论是同客观世界、物质世界、康德所讲的他敬畏与惊赞之一的“头上的星空”这个世界紧密相连的科学文化,还是同主观世界、精神世界、康德所讲的他所敬畏与惊赞之一的“心中的道德法则”这个世界紧密相连的人文文化,它们的精神层面是一致的。不过前者侧重于求真务实,后者侧重于求善务爱而已,两者最终追求的都是完美、创新。教师教书,我们读书,就是要通过授(受)业,即传授(接受)知识,在这一基础上,去解惑,即启迪思维,了解方法,从而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去传道,即升华精神。但是,授(受)业、解惑、传道这三者又不可分割,彼此渗透,相互支持,形成一体。应该说,授(受)业是基础,解惑是关键,传道是根本。正因为解惑是关键,所以朱熹在《朱子语类?读书法》中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读者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它们所紧密相连的世界不同,从而它们的功能不同,形态互异:科学文化是“立世之基”、“文明之源”,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必然失败,不能立于世;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动文明进步。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文明之基”,违背人类社会道德法则,必遭社会唾弃,人不成为“人”,文明会成为野蛮。《周易?贲卦?彖辞》讲得对:“文明以止,人文也。”正因科学文化紧密同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相连,要求真,所以在形态上,知识主要是一元的。思维主要是严密逻辑的,方法主要是系统实证的,精神主要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文化可以说是一个知识体系,要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而人文文化大不尽然,它紧密同精神世界、最终关怀相联,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还是一个价值体系,从而它的知识不一定是一元的,往往是多元的。思维不一定是逻辑的,往往是直觉、顿悟、形象的,方法不一定是实证的,往往是体验的,精神主要是求善务爱的。正因为两者的形态不同,就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例如,科学文化的思维与方法极为严谨,保证了它的正确性,而人文文化的思维与方法极为开放,不拘一格,保证了它的原创性。过于严谨,就会呆板,失去原创性。过于不拘一格,就会狂妄,失去理性。所以,在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鉴于文理分科过重,就明确指出,这只能培养“半个人”。我国有见识者一再提出,我国教育规划纲要也已明确提出,要“文理交融”。历史已证明,不仅在高等教育中,学“文”的应学点“理”,学“理”的应学点“文”,而且还应反对在中学教育中文理分科、偏科。中学这种文理分科“因材施教”是个幌子,主要是为了“应考”,更何况这种分科十分有害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培育这一根本大计。培根讲得很细:“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段话的后八个字讲得多深刻。所以,即使在高等教育中,学文科的也应该读些理科的书,学理科的应该读些文科的书。还要提到一点,在当前急功近利、浮而不实,乃至学术诚信缺乏的社会气氛中,有些学文的未必真有人文功底,未必真的了解人文精神,有些学理的未必真有科学功底,未必真的了解科学精神。
汉代刘向有句话:“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善读,固然要博览,更要有重点。善读,力求“开卷有益”。叔本华讲得对:“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不要滥读’的原则。……不如用宝贵的时间专读伟人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善读,名著要反复读。苏轼讲得深刻:“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当今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是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是知识数量爆增的时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时代。面对风云瞬息万变的时代,需要学习,需要读书,需要读好书,做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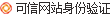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