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深秋某日,笔者访问了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与自然资源学院的J.Helmes教授在该校俱乐部里共进午餐。餐间我们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J.Helmes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林学家,已是80岁高龄,他是我的小同行,曾和Danial教授一起作为美国老一代林学家Baker教授的学生,共同编著了美国林学名著The Principles of Silviculture(《育林学原理》)第二版(1979),国际国内影响很大。交谈中,笔者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即作为林业工作者(forester),特别是森林生态和培育工作者(forest ecologist & silviculturist)都天然地自认为自己也是生态保护事业的积极支持者,然而近来却常与一些环境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意见相左,甚至引起争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针对分歧的辨析
回想当年,笔者确实是冲着森林有很多防护功能而选择进入林业系统的。到苏联留学时,笔者的专业方向是造林(森林培育学的前身),在学习过程中,笔者对林理学(后发展为森林生态学)和森林改良土壤学(后来在中国演变为防护林学、水土保持学及其他相关课程,也在广义的森林培育学范畴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回国后却最终定位在造林学中的造林部分,从此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笔者欣赏梁希老部长(我国首任林垦部部长)要“无山不绿,有水皆清”的宏大目标,并实实在在地为之奋斗过,但是近年来却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植树造林是白费功夫,自然封育的效果要好得多”;“你们年年造林不见林”;“你们造的林是绿色的沙漠”;“你们造速生丰产林是违背自然规律”等等。怎样看待这些指责?笔者认为有必要再一次进行反思和辨析。之所以说是再次反思,是因为我们不回避曾经有过的不足和错误,但也不想因此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植树造林是白费功夫?是否可以用自然封育来替代?这个问题我们太熟悉了。记得1950年笔者在北京农业大学上学时听到的第一个专业报告,就是当时的林垦部副部长李范五给森林系学生作的有关封山育林的报告。旧社会给新中国留下的濯濯童山,石头裸露,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当年的北京西山就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在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先把它们封起来,停止破坏,让它们自然恢复。封山育林本就是恢复植被的手段之一。但是,能把封山育林与植树造林对立起来吗?笔者认为当然不能。事实证明,有些地方封山育林能起到很好的恢复植被的作用,但有些地方(如土壤比较贫瘠,附近没有种源)则成效太慢,几十年还成不了林,更达不到产生正常的生态、经济和观赏价值。所以,当条件允许时,我们还是采用了植树造林的措施,让荒山更快地绿化起来。北京西山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植树造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大面积的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城市森林景观。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这样的实例,由此可见,植树造林功不可没。
年年造林不见林,中国的森林资源真的增多了吗?确实,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年代,曾经出现过年年造林不见林的情况,但是,那是局部地区在形式主义主导下一哄而上出现的恶果,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造林面积的核实率以及造林的成活率、保存率都经过层层把关验收;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都是地面调查和卫星图片(或航片)判读相结合,在几十万个样点分层抽样调查基础上得出的结果,其先进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国际上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承认。历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都说明,中国的森林资源,无论是面积还是蓄积量,都在快速增长。那些还有偏见的人可以到各地走走,就能得到验证。
人工林是绿色的沙漠?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一些生态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人们希望看到的森林都能像原始森林那样有良好的组成和结构,是复层混交林,这可以理解。但是,应该知道,不同的地带有不同的原始森林。如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和小兴安岭—长白山的原始森林就不一样。在大兴安岭北部,由于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一般都是纯林。有些地方森林早已被破坏殆尽,原始林是什么样都不清楚了。而且森林被破坏以后又经过多少年的火烧、开垦、过牧、樵采等活动影响,森林土壤早已经丧失。要在这种地方很快恢复原生态状态,显然并不现实。以北京西山绿化为例,当初造林就没有可靠的原始林榜样可供模仿。土壤贫瘠多石,只能以一些先锋树种开道,几十年后总结经验可以发现,有的树种可继续发展,有的树种就被淘汰了。想多种点原生的橡栎类树种,又谈何容易。林业工作者从50多年前就摸索着造混交林,虽有进展,但至今难成规模。总体来说,我们对大自然还了解不够,而民众的喜好(因为是风景林为主)也在发生变化,树种的选择和森林结构的培育还在不断总结中前进。树木生长得不够理想,不是人们不努力,实在是破坏历史太久,地力太差,再加上气候旱化,暂时只能这样了。其中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林也发挥了生态和社会效益,老百姓又多了许多休息的去处,总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至于有人把西昌地区由飞播形成的生物多样性不高的云南松纯林比喻为“绿色沙漠”,笔者认为持此论者应该做一些更为详尽的调查。比如,云南松是当地的乡土树种,飞播人工林的年龄阶段当时正处在竿材林时期,郁闭度大,林下植被少,但只要林龄再大些,经过自然稀疏或人工间伐,林下透光度增多,林下植被自然会繁茂起来。所以,把这种人工林形容为“绿色沙漠”,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
营造速生人工林是违背自然规律?是,也不是。速生林一般都是单树种(而且经常引用外来树种)。强度经营的短轮伐期人工林,在原来的自然界不存在,正像现代农业的麦田、水稻田、玉米地原来大自然也没有过一样。这样的人工林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速生(一般在20年以内可利用),高产(生产力水平可为原生态森林的几倍),好用(适应特定的培育目标),高效(经济效益较高),因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了快速的发展。国际林学界认为,发展速生人工林有利于在解决木材有效供给的同时减轻对天然林的开发利用的压力,因而总体上对森林保护是有利的。这个结论至今没有改变,关键在于掌握一个“度”和一个“法”。“度”就是发展速生人工林要适度,在一个大的区域范畴内,一般不超过林地总面积的10%,就能兼顾好自然保护和木材利用的双重利益。“法”就是发展速生人工林要采用适当的方法。适当的方法既包括适当选择用地(不侵入生态保护的关键地区),也包括选用适合的树种和培育措施。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应植树造林?按一般自然规律,自然景观是有地带性和地区性的,特别是水分保障程度对植被分布有决定性影响。湿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是森林,与半湿润地区相对应的是森林草原,与半干旱地区相对应的是典型草原和干旱草原,而与干旱地区相对应的是半荒漠和荒漠。从这个概念出发,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景观是草原和荒漠,而不是森林。但是自然界是复杂的,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而使气候水热条件有个再分配的格局。这就是为什么在半湿润的山丘地区常出现阳坡是草原、阴坡是森林的景观,而在典型干旱地区隆起的高山上又出现了典型的森林地带的景象(如新疆天山上的雪岭云杉林带)。再者,干旱地区的周围高山上流下融雪水与雨水径流,形成河流、湖泊。河湖周边浸润的地段又长起了森林(如塔里木河滩的胡杨林)。人们用河水灌溉种地形成了绿洲,绿洲范围内就有了发展优质经济果树的条件及保护农田免受干热风害而建立防护林网的需要。就是在干旱、半干旱的典型沙漠里,也可以充分利用沙地灌木树种(柠条、沙柳、梭梭)来抑制风沙。因此,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必植树造林的说法,太绝对了。当然,这种说法的产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林业界也确实收到了一些造林不成林的事实教训。但目前这些偏差已经有了较大改变。所以,笔者认为,提高认识,顺应自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指责,这才是应该坚持的方向。
何为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对以上问题的辨析,可以归结为如何正确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提出的第四个文明领域,这一点已获广泛共识。也有人把生态文明列为继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历史阶段的文明特征。对此,仍有不少争议。不管怎么诠释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其主要内涵应该是比较明确的。笔者认为,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其次是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包括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的建立;第三是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为前提,而不是回到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文明;最后是要有全球一体化的格局,完整的生态文明不大可能是独善其身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林业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甚至首要地位,这是合理的;但要说把发展林业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可能是言重了。因为这种说法是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狭义理解。生态建设只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已。
自然保护,包括森林保护、湿地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在内,旨在维护大自然协调、平衡的生态功能,这是一项大任务,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林业还要用它的绿色的生产功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所需的木材、能源、食物等各种林产品,还要为人类提供保健、休闲和游憩的服务功能。对于这些,单纯的森林保护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提高森林质量和生产力,提高森林的多项服务功能。因此,森林是需要培育的,育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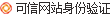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