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醒民
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认为,科学与民主、自由不是对立的两方,而是孪生兄弟。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是与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一致的,进而具有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精神气质。
科学与民主、自由具有一致性。默顿在论述科学精神气质时就表明,科学和民主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民主的精神气质把普遍性作为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指导原则包括在内。”“科学的普遍性蕴涵的成就评价的非个人标准和社会地位的不固定,描绘了民主社会的特征。”莫兰在阐明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论基本原则——客观性原则、检验原则和事实上的证伪原则,这一切都是按照公认的游戏规则进行的——后得出结论:“科学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好的民主社会。”
在这方面,布罗诺乌斯基的阐述更为详尽,他强调科学共同体具有自由、民主的气质和稳定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科学共同体,讲他的心智,倾听和反驳。科学共同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没有一个教条的社会能够具有这种稳定性。尽管今天的科学理论与往昔相比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科学家的社会没有随之倾覆,并依然尊重不再拥有其信念的人。莱维特注意到,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历史的和逻辑的纽带:“一般的规律是,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中任何一个的热情爱慕者都倾向于以同样的热忱来支持另一个。这两个概念历史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内在逻辑而被联结在一起的。”
确实,科学与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是互为因果条件的,并且在历史和地理上是巧合的——共时同地成长和确立。这些新观念的出现和确立,或多或少是在同一地方——西欧,并在大致相同的时期——约在1600年至1800年间。科学与民主、自由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三者在内涵和精神上的一致、历史和逻辑的联结,而且也表现在科学与它们的相辅相成的互动上。
先看民主、自由对科学的推动作用。默顿揭示,科学精神气质为一个暂时性的假设奠定某些基础:“在与科学精神气质一体化的民主秩序中为科学提供发展机会。”西博格在审查自由和科学的关系后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是在自由之上茁壮成长的。人的好奇心、对真理的追求和新观念的应用,似乎在没有束缚的、存在激励和因好工作而受奖赏的环境中才能得以最佳地发展……在许多方面,自由的本质和科学的本性是平行的。”当然,正如西格里斯特(H. E. Sigerist)所说:“不可能在民主与科学之间建立起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能说唯独民主社会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土壤。然而,科学在民主时代的实际繁荣,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
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科学对民主、自由的促进作用。莱维特对此有精湛的研究。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断发展的科学精神如何设法促使社会朝着自由价值观念——对绝对主义和权威专制的反对,对世袭特权的否定,对更宽范围的思想领域的开放以及传统的非神圣化——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缓慢扩散的过程,自由主义理想不断传播,它与科学家以及科学修养很好的人的最初联系逐渐断绝。虽然如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成功的科学很少归功于反自由的价值观念。他合理地推测,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这样一些人持续增长,他们精通科学,熟悉科学方法,并理解使科学得到发展的必要思想框架,他们的存在把自由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欧洲和北美(最终到全世界)受过教育的人口之中。由此产生看待权威、思想自由以及精英原则的种种态度。自然而然,有一些著名人物,他们对尚未成熟的自由主义的支持与他们对科学的热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容易想起如伏尔泰、百科全书派、莱辛、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
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科学、民主、自由可谓三位一体。西博格一针见血地指明:“我相信,科学社会和民主社会不仅是相容的,而且科学和自由的合作向我们提供达到我们大多数人今日追求的那类世界的最大可能性。我也相信,如果自由的人想要生活在现代的科学时代,享受它的好处并控制它的命运,那么他们必须随那个时代成长,他们必须教育他们自己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他们必须通过教育发展他们向着最高理性的、人道的和伦理的行为。”而且,科学与民主(以及自由)这些词语本身似乎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们能够超越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自然而然地自行其是。
这里也存在表面上的悖论。表面上的悖论在于,一方面科学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是普遍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科学也是有社会结构的,有不平等的分层与权威的存在。这二者怎样一致起来?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权威结构的存在,才能维持科学共同体的意见一致;而只有这种意见一致,才能保证科学中的普遍性原则及民主精神的实现。他们强调指出,科学中的普遍性和民主精神就表现在:在科学评价系统中,以统一的尺度来考察所有科学家作出的成果,以普遍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科学家的工作质量。
也有反对意见认为,科学与民主、自由是对立的,科学对民主、自由构成威胁。公正地讲,这些反对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也是值得科学的辩护士和卫道士警惕的。但是,由此而把科学置于民主、自由的对立面,则明显失之偏颇。因为所有这些弊端或是由科学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纠错机制失调、科学共同体监管不力引起的,或是由科学异化导致的,而并非科学本身所固有。更何况,把科学和技术说成是暴政的同盟军,更是无稽之谈。塔利斯的反驳是中肯的:科学在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奥威尔(Owell)的《1984》的读者可能认为,发达的技术为发达的暴政提供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塔利斯以对具体事例的分析,驳斥这种看法。他说,从真理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历史表明,没有遍及全国的电子通讯系统,暴政能够达到骇人听闻的完备。
高技术可以被用来帮助压迫,也同样可以用来支持民主。近几十年,在科学落后的国家,惨不忍睹的暴政持续不断。最有力的暴政同盟者不是科学,而是束缚于习惯,是作为其最高表达的科学的那种批判传统发展得不够。事实上,高技术很可能像支持暴政那样支持民主,信息传送的现代方法对民主、对权力扩散和公正所起的作用至少像它们对暴政一样有效。
(作者系澳门赌场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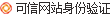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