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保军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人,诗意地安居》是一部生态文明经典著作,“诗意地安居”是海德格尔提出的重要理念。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人们越来越多地“安居”在城市,当今的城市真的满足了人们“诗意”的需求了吗?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在他看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正面临着核心价值的转变。
向生态文明“转身”
《中国科学报》:您曾在谈到我国城市规划的未来时强调:我国未来10年城市规划的重点应该有所转变——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请您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转变?
杨保军:规划工作重点的转变,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决定的,也是以往暴露出来的问题,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在进行城市规划过程中,要考虑并解决很多问题,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问题的排序是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物质极度短缺的时代,因此社会对“物”的渴望很强烈。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我们和很多欠发达国家一样,如何更有效地创造财富,在规划工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排在首位。因此,以往的几十年,我国的规划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崇拜效率、GDP的特征。
这种“以物为本”的理念,以往没有遭到太多的反对。如今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了,我的生活质量、我的生活感受是否也提升了呢?”在这种反思面前,人们发现经济的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升,两者并没有很好地对应起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感受得到应有的关注。
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更关注“物”的工业文明,向更关注“人”的生态文明的转变。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也再次强调了这种转变。
《中国科学报》:“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城市规划上该如何体现?标志是什么?
杨保军: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核心价值的转变。以这种价值转变,反观我们以往的规划,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以道路为例,我们以往在道路的规划上,体现的就是物的思想。
首先道路非常宽阔,其最大受益者是汽车,可以使它快速通行,而过于宽阔的道路,给步行者的通行带来不便。通常道路要满足三类通行:汽车、自行车、行人,汽车是“物”,为了更快地创造财富,本来就很狭窄的自行车道,还让出了一块供汽车使用。“人”的空间被挤压了,可供步行的街道,正逐渐消失。
现在西方倡导一种理念:可步行的城市,也就是说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应该有足够的空间供行人穿行,而且是悠然自得、饶有兴味地穿行。
尊重规律 尊重自然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城市规划主要应遵循哪些原则?科学?美学?如何相互作用?
杨保军:城市规划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一门科学,它不具有可重复性,但它具有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一些规律是必须遵守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最为关键。
前段时间,在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中,一些城市遭受灭顶之灾,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建设中违背了自然规律,在自然条件不适当地方进行了建设。
再来看经济规律。以鄂尔多斯为例,这个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大规模的建设量游离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之外,是一次“资本游戏”,因此经不起经济规律的考验,走向危机是迟早的事。
从社会规律看,目前我国正处在必须反思社会公平的阶段。城市规划不仅要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兼顾社会公平,也是十八大关注的问题之一。
城市规划在科学性、合理性的问题解决后,才考虑到美学。我认为,城市的规划者和建筑者要有艺术家的情怀,而真正的艺术家最懂得尊重自然。规划艺术也是在自然、文化、功能三者间寻求平衡的艺术。
《中国科学报》:与发达国家相比,您认为目前中国城市规划存在哪些问题?
杨保军:国际比较是一个很慎重的课题,所谓比较要有一定的相似条件。城市规划与自然科学不同,涉及众多制度和文化的因素。因此,我这里所说的更多的是“差异”,而不是“差距”。
西方国家早已度过了工业文明阶段,城市化已经达到了70%~80%以上,不再面临大量的农民向市民转变。环境问题在西方也更早地暴露出来,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西方的重视程度也高过我国。
此外,西方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稳态,空间形态基本定型。西方的城市规划不以“增量”为主,而是以“存量”为主,很少有大规模的新建项目,而是更多地对已有的城区进行优化、更新、改善。
东西方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差异。更主张民主的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上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意愿,在确定一个规划方案前,必须和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对话,往往一个小项目要谈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这些差异导致我国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与西方国家的关注重点和方法都不太相同。
目前,我们逐渐遇到和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公众参与方面,我国的公民也越来越多地有了参与的诉求,以往完全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企业精英进行决策的模式,也正面临着改变。
固化的文化梦想
《中国科学报》:以北京为例,不少建筑、景观缺乏审美价值或与周围景观不协调,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
杨保军:一位法国建筑大师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追求着什么。”城市代表了一代人在一个地方的梦想和追求,一种价值判断,建筑风格不协调,说明了社会内部价值观存在一种不协调。
从审美上说,我们的社会在现阶段,的确比较浮躁,沉不下心来表达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美,于是只能更注重形式,而这种对形式的追求,又往往被简单地表现为对“前卫”“时髦”的膜拜。
“为什么建筑不能赶时髦?”是前段时间在规划界、建筑界争议颇多的话题之一。我个人认为,少量的、与文化领域相关的建筑赶一下时髦,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为后世留下一个时代的印记。但是我不认同大量的建筑都去赶时髦的做法。“时髦的大多是短命的”,对此,时尚服装、流行音乐,很能说明问题。而服装和音乐,可以轻易地被抛弃、被淘汰,而建筑是一项百年大计,应该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中国科学报》:我国城市化速度很快,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杨保军:越是大规模建设越要尊重自然环境,为了建筑城市,大规模挖山填海,这是很危险的。以往人们太过自信,以为人类可以控制、改造自然,这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了。真正建立起生态文明观,必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二,越是大规模建设,越是要考虑建设是为了什么。在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我想谈谈尊重文化的问题。越是大规模建筑,越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不能简单地“以新代旧”。
人类从过去走来,并继续走向未来,历史是连续性的,保持文化的连续性,是每一代人在历史面前的责任,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历史文化的价值更加凸现。
从城市规划上说,一个城市可能很大,但真正值得人们去的地方并不多。我个人在休闲的时候,会选择去锣鼓巷、什刹海这些有历史情怀的地方。
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也要满足人们这种怀旧、寻根的需求。
《中国科学报》:目前一些学者认为,在我国城市规划上,政府决策产生了过多的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保军:一个合理的城市规划,要用四种力量介入: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政府是一个规划项目的源头,政府有需求展开一个项目,然后专家来进行合理性评估并设计出科学性方案,其中涉及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公众参与进行对话、沟通,最终出台一份完整的项目规划。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四种力量很不平衡,有些领导过于自信而排挤了其他几种力量,甚至是专家的力量。有时,这种不平衡导致了决策不科学、不合理,使最终出台的规划方案,存在较高的风险。
针对这种问题,一些地方开始进行探索与尝试,比如建立组织规划委员会,来保障各种力量的平衡参与。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未来发展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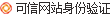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