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界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划界的实际意义即划界在科学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中的实践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科学划界或科学分界是科学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划界(demarcation)一词在英语中的含义是“划界、分界、定界、划分、区分、界限或界线”之意。所谓科学划界,指的是在科学与其他知识体系、社会活动和建制之间的划界,特别是与非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它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在科学与它者之间是否可以划界?若可,如何划界?划界的标准和意义何在?波普尔对科学划界相当关注。他说:“找到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够区别经验科学为一方与数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具有悠远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一对分界标准:科学通过其原理的确实可靠性而与意见、迷信区分开来;通过其对第一因的理解而与工艺区分开来。17世纪划界主义者的感觉能力发生巨大变化。当时大多数思想家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条分界标准(区分确实可靠的科学与可错的意见),但是拒绝他的第二条分界标准(区分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例如,从伽利略、惠更斯、牛顿的工作中就会看到,他们宁可不要由第一原理或第一因导出的理论知识,而要经验知识。尽管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思想家之间存在方法上的分歧,但是人们普遍同意科学知识是确实可靠的。培根、洛克、莱布尼兹、笛卡儿、牛顿和康德都赞同这种描绘科学的方式。他们也许在如何精确地证明知识的确实可靠性方面意见不一,但是并没有对科学与确实可靠的知识是相通的这一断言有过疑义。随着认识论的可错视角的出现和最后胜利,人们像19世纪中叶大多数思想家那样承认科学并不呈现确实可靠性,并且所有科学理论都需要修正,须经严格校订,那么企图用区分知识和意见的相同方法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就不再是可行的了。于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很快就锻造出能承担这一任务的工具。像孔德、贝恩(A. Bain)、杰文斯、亥姆霍兹和马赫那样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开始认为,真正把科学与其他东西区别开来的是方法论。20世纪的新分界主义传统也力图解决分界问题。维也纳学派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句法上即逻辑上的探讨。逻辑经验论的推理表明,如果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无能为力,那么意义理论也许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在逻辑经验论之后,特别是在当代,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划界问题观点——划界论和反划界论。反划界论者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之间根本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因此无法在科学与它们之间划界。不少哲学家坚持反划界论,他们怀疑能够找到任何可能辩护的划界原则。
不管学人的观点如何多样和分歧,划界问题毕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而且划界的实际意义即划界在科学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中的实践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划界有助于维护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权威和共有价值,提高科学理论的同质性以及科学的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一致性,矫正与公众的关系。贾撒诺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某个智力活动领域被贴上“科学”的标签时,那些非科学家群体事实上被禁止对科学发表任何实质性的意见。同样,给某种东西贴上“非科学”的标签(比如政治),就是剥夺它的认知权威。吉林洞察到: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界或聚焦于“边界工作”实践,“为的是把被选出的特征赋予科学的建制(即对它的实践者来说的方法、知识储备、价值和工作组织),为的是构造把作为非科学的某些智力活动区分开来的社会边界”。他还论述说:“一种普通的划界活动是内部人员尽力把那些不合格的成员从他们之间驱逐出去。内部的科学家给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贴的标签形形色色:离经叛道的人、伪科学家、业余爱好者、骗子。那些遭到排斥的人一般都具有‘真正的’科学家的外表,而且他们自己也相信自己的确是真正的科学家。但是,内部人员把他们定义为装腔作势的人,他们非法地利用权威,这种权威仅仅属于科学文化空间的真正居民。这些社会控制机制威胁内部人员说,明显地偏离规范将遭到放逐,因此这些机制无疑提高科学信念和实践的同质性。对离经叛道者的制裁也是矫正与公众的关系的机会,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在享有权利的社会民众中恢复下述信念,即科学本身有能力剔除冒名顶替者(所以请不要插手);它也可以恢复这样的信念,即科学实际上正是真正的内部人员所说的那个样子(不会有任何肮脏的事情)。”多尔比在回答“科学家和其他人为什么希望划定边界”问题时宣示:“自我界定的群体十分经常地在它自己周围建设边界,或者非正式地以各种成员标志夸示(如谈吐、使用特殊的行为或服装),或正式地以各种成员标志夸示(例如一些职业利用教育资格证明和证明合格的成员资格)。以这种方式,他们能够排除可能降低或削弱群体共有价值的局外人,他们能够在群体内坚持标准和团结一致。该状况在科学中也是类似的。”
其次,划界是为了保护科学内部的资源和特权。吉林揭示出:“科学家的最后一种划界活动是修筑围墙,从而保护内部的资源和特权。这种划界活动能否成功可以通过外部权力在控制科学上的阻力来衡量,或者换一种说法,可以通过内部科学家保护自己对科学的自主控制来衡量。”
最后,划界能使科学家致力于科学问题的研究,而不在非科学或伪科学问题上争论不休、耗费时日、白费气力。划界也使部分科学爱好者、科学迷、伪科学的制造者和追随者清醒过来,不再沉溺于无意义的或无结果的非科学问题(他们误以为这些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无谓地消耗社会资源和个人生命。
不用说,在具体的划界案例上或率尔行事,或措置乖方,或操之过急,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摧残科学的生长点,扼杀科学的萌芽,遮蔽科学的新视野,阻碍开拓科学研究的新领地,挫伤科学爱好者的积极性。确实,对科学划界理解的偏差和做法的失当会引起消极后果,而且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值得引起当事人的警惕。
(作者系澳门赌场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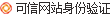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